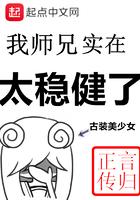奇书网>北京城与人读后感 > 三 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第1页)
三 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第1页)
三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
我们不得不使用如“北京文化”一类较大的概念于具体的现象分析,这也是论证中难以避免的语言问题。京味小说所写,主要为北京的市井文化;至于北京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学术文化,不能想象成为文学的对象。然而文化价值却又非因其为“市井”即见低下。市井文化中完全可能含有对于说明中国文化特征极有意义的东西。不论老舍还是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在其对北京文化的发掘中,都展示了乡土中国的重要方面;具体题材、所描写生活琐屑的“小”中,都寓有“大”。艺术创造的特殊要求使他们依赖于个别性,材料的性质与时代思潮却总是把意向导向广远,使其追寻一般、普遍,如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有人谈到老舍的满族气质和其作品中的满族文化。我毫不怀疑这种研究的价值,却以为在老舍开始创作的那个时代,拥有了老舍那种教养的现代知识者,其具体民族意识(如满族意识)或许比之当代人更为稀薄。至于当代作家,他们的某些作品虽格局显得狭小,却凭借自己相对狭小、严格的文学选择,在某个特定方面(如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开掘中,达到了北京文化的深处。即使分别看来显得单薄,同时期一批作品在一个方向上的掘进,所达到的,或许是老舍那一代人虽及于却因判断失之简率而未能深入的。这些作品展示的北京文化,有可能是既富于美感又富于意义含量的方面。
我们不妨抽出几个侧面聊示一般,看老舍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在他们的北京描绘中,提供了哪些北京文化的特征性描写,以及超出了地域文化的东西。
家族文化
关于京味小说对传统社会家族文化的发掘及发掘中的优势与缺欠,上文已多所谈及,这里只需做一点补充。
冯友兰说过:“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11〕“五四”时期家庭伦理小说流行,礼拜六派的刊物上亦常有这类小说刊载。初期新文学大多是由家族对于青年知识者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要求的压制这一有限方面呈现家族形象的,对于家族制度的功能的理解,也限制在纯粹而又狭窄的道德方面。到30年代,如冯友兰那种对于家族制度的理解才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激流》等作品的产生即以此为条件。老舍以其面对北京市民社会的特殊便利,呈现了多种中国式的家庭形态,展示了它们共有的封闭、自足(与外界缺乏交换)等文化特征,以及这种传统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瓦解、重建过程。写家族伦理,新文学史上不乏其人;而跟踪观察传统家庭,探索其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并由此引出“家—国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重大命题的思考,由家庭改造引向民族生存方式改造的大主题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这里值得注意的,也是由家庭伦理问题到人性、民族性格改造的问题,由家庭变迁,个人与家庭、国家间关系的变迁到民族生活的变革的由近及远,由具体及于普遍,由狭小及于广大的思路。与较为单纯的《激流》立意(反封建)不同,经由家庭,老舍探究整个中国的命运,由北京沦陷前民族危机(透过家庭危机、人的精神危机呈现),到战火中民族再生(同样透过家庭在解体中重建来表现),写出了当时的家庭伦理小说所可能有的较大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含量。
这自然不是人为扩张。家族伦理是一整套传统文化哲学的基石,《离婚》中张大哥的哲学以婚嫁为基点推广而无所不至,是对于上述事实巧妙的艺术概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只有在这种伦理现实中,张大哥的家庭纷争才具有社会历史以至社会政治的含义,整部小说才成其为中国社会的象喻。老舍所追求的,正是情节所负载的上述喻义。
在对于人伦关系的具体表现中,老舍使你看到,这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为了家族生命的延续,必然以其成员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即使小羊圈祁家这种非标准化的大家庭,个人也只有在其与家族的关系中才能肯定自身。对于个人价值的判断不能不依据家族利益的尺度,尤其其中的女性。“宜室宜家”,是传统社会之于女性的起码要求;韵梅(《四世同堂》)那位批评着“北平文化”的丈夫,以至小羊圈世界的创造者老舍本人,最终都不能不在这一意义上,肯定人物的存在价值。这类思考的困境是作品中真正深刻之处,这儿才有思想的潜藏量。老舍作品中的有关议论的价值,也在于对其思想困境的披露,在于由议论的重复与无力透露出的矛盾在实际生活中的难以解决。
老舍没有为传达思想、意念而将“生活”极端化。他不选择极态,所写是中国式生活、人生中较为普遍的状态。〔12〕寻常状态中的普遍伦理关系,普遍人生,其中或许也寓有更“现实”的中国?历史毕竟已推进到现代,家庭关系毕竟在历史地改造着。因非“极态”而更显出顽梗的伦理事实,其中包含的悲剧性才是真正令人惊心动魄的吧。即使在对家庭场景的描绘中,老舍也无以统一他的理性与情感判断。他不能不在表现那些贤淑女子的悲剧境遇时欣赏她们的贤淑和颂扬她们的自我牺牲。这无意中敷染了更浓重的悲剧色彩,复杂化了作品、形象的意味。老舍以其作品,更以其注入描写中的自身矛盾,经由家庭形象,把中国社会在进向“现代”途中的实际困境,把生活中不能不延续下去的伦理痛苦艺术化了。
京味小说在老舍之后,一致表现出长于描写家庭生活的特点,关于青年的认识与描写则远远超出了老舍当年的眼界与见识。包含其中的伦理思考容或没有老舍创作的尖锐性,却保留了尊重生活、非理念化,和选择、表现中的自然。这些作品的有关价值也在所提供的形态的多样性和描写的细致入微上。“思想”不免会是时期性的,艺术化的人生形态或许更有长久的生命。
商业文化
一如长于描写家庭生活场景,尤其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京味小说——无论老舍还是当代诸家——也长于表现传统的商业活动场景,“老字号”,以及胡同里小本经营的坐贩行商;长于写旧式商人,他们的商业作风,旧式商业的格局、情调。“老字号”属于乡土中国。“中国的传统商业是家庭单位的店铺与家庭资本、家族管理的行号。”旧式商业,其经营方式及有关的商业道德、对商业行为的社会评价方式,带有宗法社会的鲜明印记。这种商业是老北京作为消费城市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不能不在意欲呈现北京文化的作品中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
似乎是,凡经验过老北京生活的人,总会对那些老字号,那些商贩、公寓老板不能忘怀。“三合祥的金匾有种尊严!”(老舍:《老字号》)。北京城老字号的招牌及其古旧情调,店铺的悠闲气氛,胡同深处小贩别致的叫卖声,都成为古城风物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韵味悠长的一部分。周作人看老店铺的招牌油然而生“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14〕林海音写梦里京华,对走街串巷“换绿盆儿”的记忆犹新。〔15〕《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中几处写到卖冰的小贩风味独具的经营方式(“铜盏敲冰卖”,“忽听门前铜盏响,家家唤买担头冰”)。《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记清代北京元旦盛况,“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间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最难忘的,是这市声。在流寓他乡的北京人,“铜盏敲冰”或许是最宜入梦,最足作成“思乡的蛊惑”的了。那才是熟悉温暖亲切近人的北京。〔16〕
瞿秋白曾说到“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所谓商人”,不同于“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的老板”,他们是所谓“小商界”。〔17〕同属“中国式”,发展到近现代,其间也有规模的不等。“北京的买卖家,大小之分犹如天上地下”(刘进元:《没有风浪的护城河》)。在京味小说作者,却像不大长于写显贵要人,他们也不长于写富商巨贾,熟悉的是较“小”的一类,而非同仁堂、瑞蚨祥那种“资财万贯,日进斗金”的主儿。即使老字号,如王利发的茶馆,也仍然是“小”的。这是一些属于胡同世界的买卖人。
消费的北京,从商是胡同里的寻常职业。京味小说所写,首先是道地的老北京人。老舍写经营布店的祁天佑(《四世同堂》),写开茶馆的王利发,短篇则有《老字号》、《新韩穆烈德》;汪曾祺写小酒店情调;邓友梅写小客店主人(《烟壶》),写“跑合的”(《寻访“画儿韩”》、《烟壶》);苏叔阳《画框》写小本生意人;刘进元《没有风浪的护城河》写炕头上设摊做买卖的胡同老人。写市场、商业活动场景而备极生动的,还有《烟壶》中的德外鬼市。虽非正宗京味也京味十足的《封片连》、《鬈毛》,则把当代北京的个体商场,写得声态并作,一派火炽。
更有文化—风俗意味的,自然不是店铺招牌,而是那种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人情体贴是一种商业艺术。老北京商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礼仪文明与十足的人情味。〔18〕“三合祥虽是个买卖,可是照顾主儿似乎是些朋友。钱掌柜是常给照顾主儿行红白人情的。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门凳上常坐着附近最体面的人;遇到街上有热闹的时候,照顾主儿的女眷们到这里向老掌柜借个座儿”(《老字号》)。“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祁天佑,有一张典型的商人面孔:“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四世同堂》)。和气的商人,是足增人间的暖意的。“卖烧饼的好象应该是姓‘和’名‘气’,老李痛快得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到末日!拿出一块钱,唯恐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也没有,客客气气地找来铜子与钱票两样,还用纸给包好,还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离婚》)。有时因店铺伙计太和气,太会拉主顾,以至使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离婚》)。和气与耐心是经营艺术,也是老派市民的修养。即使买卖不成,凭着“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他们会“把失望都严严地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四世同堂》)。〔19〕
当这种时候,京味小说只写方式、情调,商业关系已在其中。这种交易依赖的,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商业契约和**裸的利益原则。〔20〕因而营商得凭借“外场工夫”;商店的装潢华丽比之资产、货色更易于显示信用。对此清末笔记中亦有所记。邓友梅笔下的估衣行情景,在当今的年轻人或觉匪夷所思的吧。“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饭,晚上照例得听戏”(《〈铁笼山〉一曲谢知音》)。讲求信义、人情,以非商业手段达到商业目的。
让人留恋的有时只是情调。《老字号》所写那种宁静悠闲的古旧商业情调,几近于抱雌守虚清静无为的哲学境界。“多少年了,三合祥永远是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上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此外,没有半点不像买卖地儿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有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三合祥是与古城一体的,且比之胡同更多着些端肃与庄重,更有陈年老酒般的气息。〔21〕
茶馆老板王利发(《茶馆》),几乎可以看作古老商业传统的人格化。作为旧式生意人,他几乎是太完美了。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合于礼仪规范,不合于这种社会对于一个商人的道德与行为要求。他即茶馆。茶馆的风格、面貌,几乎只系在王利发的个人风格上。
相对活跃的消费品市场和极端保守的商业经营方式,相对发达的商业与极不发展的近代商业观念,构成近现代中国奇特的商业文化面貌,并不独北京为然。老北京除有数的老字号外,商业规模的普遍狭小,也正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制约的结果。限制了商业文化现代化的,与限制着宗法制家庭解体的,是同一个乡土中国。以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低下为前提的生活水准的相对均衡,也限制着商业活动的规模。京味小说所写北京商人传统的商业伦理,即反映着中产市民保守的道德要求。
一种在现代人眼中极奇特的现象是,以盈利为追求的商业活动,却千方百计掩饰其本应公开申明的商业目的。传统社会世俗心理中的商业道德,制约着上述真实的商业目的的实现,或作为这种目的的遮饰物。《没有风浪的护城河》以不图赚钱的小本生意人祁家老祖儿作为“变着法儿坑人”的摊贩的道德对立物。祁家老祖儿,“那叫多仁义,多厚道!”这是胡同居民(包括作者)对于一个生意人的道德评价,使用的是胡同里通用的一般道德尺度,这种尺度是不关心商业效益的。〔22〕祁老祖儿式的“仁义”、“厚道”,也顺理成章地以“不大会做买卖”为条件。
《牛天赐传》并非写北京,其对于牛老者的描写却反映了老北京人及老舍本人评价商人所持标准。牛老者“是天生的商人”,他中庸、谦和而悠然。他的经商不凭借商业智慧,他靠的是一种“非智慧的智慧”,近于奇妙的本能。“对什么他也不是真正内行,哪一行的人也不诚心佩服他。他永远笑着‘碰’。”“他有这么种似运气非运气,似天才非天才,似瞎碰非瞎碰的宝贝。”悠悠然使他显着点儿飘逸,不俗;非内行则让他保存一些天真,平易。中国古代史传、笔记中的风雅商人无不有非商人气质以至名士气,这里有早经形成的评价商人的士大大标准,所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戴节妇家传》)。非商人本性的商人才是好商人,道德感情上可以接受的商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