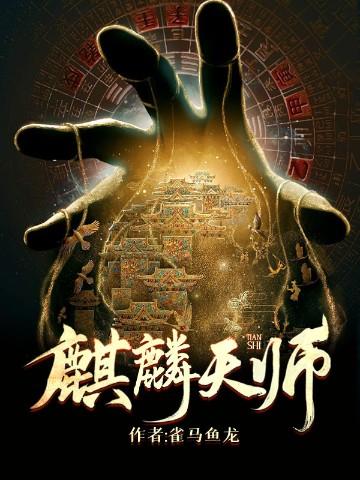奇书网>史官是当时社会上怎样的群体 > 四重于事死(第1页)
四重于事死(第1页)
四、重于事死
南宋社会人们很重视墓葬问题,其特点是:
(一)重视墓地的选择
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上最庄严、最经得起岁月磨练的纪念性建筑是陵墓。人们非常重视对于陵墓地址的选择,要有山有水。埃及的金字塔矗立在尼罗河西岸,金字塔宛若天然生成的一座山峰,给人以神圣、威严的感觉。印度的泰姬陵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陵墓,这是一组大建筑群,除有清真寺外,还有各种建筑相衬托,其中有个十字形的中央水渠在花草丛中纵横,使墓区更加冰清玉洁。中国各朝统治者在生前最为重视的一件事就是开始注意寻找“风水宝地”作为陵寝之所。
中国现存的最早皇帝陵墓当属秦始皇墓,它的主体在今陕西省临潼骊山主峰的北麓,外观为一方锥形夯土台,陵体内却十分豪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描绘,墓室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简而言之,始皇陵与山水也有着不解之缘。西汉的皇陵大多兴建在陕西咸阳至兴平一带,除重视内部装饰外,更重视把有山有水作为一个标准。找寻风水好的宝地作为帝王陵墓的习惯就始于汉代,陕西境内汉唐的陵墓都有这一特点。唐朝时更是以自然山体作为陵本,较过去的人工封土更胜一筹,如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选在位于陕西乾县境内梁山的最高峰,气魄比前朝的陵墓更大、更壮观。明朝有十三陵,除明太祖朱元璋在位31年,死于南京,陵位建于南京城东钟山的主峰外,迁都北京后,自明成祖朱棣开始,先后13位皇帝的陵墓都建在北京昌平区以北的天寿山南麓,这里东、西、北三面山势环抱,南面地域开扩,形成中国历史上环境优美的、各座陵墓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气势宏伟的一个最大陵区。清朝顺治帝在河北遵化燕山修建了清东陵,雍正皇帝认为此地风水不佳,便在河北易县泰宁山下修建了清西陵,以至形成清帝两陵并列神州的格局。
位于今河南巩县境界的嵩山与洛河间有北宋的8位帝王的陵墓。宋朝皇陵制度与前朝最大的不同是从建陵到下葬应在皇帝死后7个月完成,而且,宋朝又有战争不断的时代背景。所以,它虽然也是选择在面嵩山而背黄河、洛水,是一些“藏风得水”的好地方,选择在面向远山丘陵处,利用中原大地南高北低的趋势,也都符合帝王选墓址的严格要求,但是在建筑的规模、风格和布局上都不如前朝,甚至比不上一些富商、地主的墓葬。
南宋的帝王却连如此要求都不能达到。地处今浙江绍兴的南宋六帝陵墓大都为临时安厝地,因为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日后回归中原上,所以,南宋帝王墓葬地不如前朝恢宏,墓葬等级也较前松弛。这些陵墓元朝时遭到严重破坏后,至今在地面上已无痕迹可寻。这是南宋社会的一个遗憾。
由于明州史氏家族在南宋具有“一门三相二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显赫地位,功勋卓著,情况特殊,家族又重视墓地的修建,整个家族墓道呈现出王者的气势,这些墓道至今仍基本保持完好,它从另一个方面可以弥补南宋皇陵的遗憾和不足。明州史氏家族认为墓地是家族声望和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为风水好坏是关乎一个家族兴衰的因素,因此必须重视对于墓地的选择。
明州史氏家族墓地位于浙江宁波东钱湖的东面,基本上构建在浙江省鄞县的东南部山区。墓地以高356。2米的福泉山和556。2米高的望海峰为其背景,让上、下水溪作为它们的分水岭,含括四周的大慈山、双峰山、青龙山、太阳山等山地,“从下水绿野岙、穆公岭、响铃山、安乐里山、黄梅山、采坑、金家岙,再到庙沟后、象坎山、隐学山直至高钱青雷山、月波山与东吴的古野岙、宝华山等处,方圆30多里”[1],明州史氏家族多以一个小家庭共同葬在一个墓区,且把“地丰浓肥、墩厚、草木盛茂、平稳之地”作为选择墓地最好的标准,形成群山环抱、山山拥翠的气势,同时利用东钱湖及其大小支叉环绕其间的优势,造成天水相接、自然景观秀丽多姿的美景。其间还有寺、庵建筑相配置,使墓地在庄严肃穆中更呈现着神圣。
从明州史氏家谱记载和实地考察可见,史氏家族墓地集中在群山之中约有九处之多,各处墓地相距不远,紧临福泉山,面对福泉溪,背山面水,确实是一风水宝地。史才、史浩,史渐、史弥远家族、史弥忠、史岩之等所建墓地群,始终把风水的好坏作为选择墓址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与水文相结合的优点。我们从研究明州史氏家族的墓制中有利于加强对南宋墓葬制度的认识。
(二)提倡“事死重于事生”
《中庸·达孝》章中说:“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明州史氏家族提倡子孙们“养则必恭”和“祭则必敬”,既要在父母活着时以孝事生,更要在祖先亡故后认真事死,让敬祖先的孝道观念贯穿一生。
南宋时期,与明州史氏家族一样,仕宦豪绅信佛者很多。而且当地禅寺林立、高僧辈出,展现了佛教的鼎盛。佛教提倡“菩萨应生孝顺心”与“慈悲心”,主张生前应注重父母的恩德,强调父母死后也不应忘记他们的恩重如山,体现了佛教、佛事对“孝道”和墓葬的影响。史浩不仅担任南宋宰相,也是一个佛教信徒,他把信奉佛教与传统道德的孝心相联系。史浩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众,一生吃斋念佛,笃信佛教。1173年(乾道九年),史浩途经江苏镇江,到了金山寺,观看了当地寺院在做水陆道场。所谓水陆道场,就是寺院应施主的要求,为死去的人诵经、礼佛,追忏亡灵、寻求超度灵魂而举行的一种佛教法事活动。此俗始于梁武帝时期。它是集佛堂音乐、诵经、拜佛,以及绘画、书法、雕刻、舞蹈等各种文化活动为一体的一个集中展示,也是费时、费钱、费人的一项活动。史浩观后羡慕其“水陆斋法之盛”,回鄞县后即施田百亩,在东钱湖月波寺、尊教寺、青山寺和无量寿庵修建了南宋最大的四时水陆道场,并亲制疏辞,撰集仪文,以报四恩,凝聚了对于祖宗、父母的孝心。宋孝宗见其诚心可嘉,特赐“水陆无碍道场”御书。“水陆道场自此在浙江鄞县流传”开来。[2]随之成为习俗,自南宋开始至今不绝。
史浩的母亲每年都要去普陀山朝拜观世音菩萨,认为观世音菩萨的神力大慈大悲、乐于救苦救难,保佑今生与来世,只要人们呼唤,就会大力相助。有资料表明史浩与普陀山、与观世音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资料中记述了一桩奇事,说的是绍兴十八年三月,史越王以余姚尉摄昌国(今浙江定海)时,有一天天将暮,有一长僧来访,他说史浩将来会做大官,直至当太师。又说,你的一生肯定有好的结果,能作宰相,若官家要用兵打仗时,切记要尽力劝谏。说完遂即告去,出门就不知此人的去向了。二十年之后,史浩在普陀山遇到的事,听到的话,嘱咐的事情,居然全部实现了,一点不差。由此他从虚幻中感受了普陀山之神奇和观世音菩萨的威力之巨大。古籍中神化皇帝的做法,那些虚构的溢美之事居然也会使史浩更加相信普陀山的神力,他“完全将明州之补陀山认定为佛经上讲的补陀山,认定为善财向观音问法之地,这等于认定此山的观音道场的地位”[3]。
1178年(宋淳熙五年),史浩见母亲双目已失明,难以实现每年都到普陀山去礼佛的愿望,于是在东钱湖月波山旁修建月波楼,并在岛上凿山为洞,垒石成岩,修建了“宝陀洞天”,还在洞边建一“霞屿寺”,并供奉母亲所崇拜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满足母亲的需求,还模仿修建了近似普陀山的观音道场。这样,每当母亲洪氏想去普陀朝圣时,史浩就让她先在东钱湖上乘船,亲身感受船只的颠簸,亲耳聆听风啸与浪声,之后,登岛至“宝陀洞天”与“霞屿寺”,使老人家也能有到普陀山崇拜佛祖的感觉,满足老人渡海参拜观世音菩萨的诉求。宋孝宗为史浩的孝心所感动,特此赐额为“慈悲普济寺”。[4]
史浩为此也曾赋诗一首:
“行李萧萧一担秋,浪头始得见渔舟。晓烟笼树鸦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
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对月波楼。于今幸遂归湖愿,长忆当年贺监游。”
此寺后经废弃与多次修缮,1989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已将“小普陀”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游客、香客与日俱增,现已成为一个难得的旅游和宗教活动场所。
事死如生说明,亲人的去世,人们会像他在世时一样,百般“孝顺”他,尊敬他。具体表现在他死后与生前没有区别,如死后要重葬,要表现出痛苦,要在日后的年节中不断祭祀。南宋时仍有按亲疏远近不同的关系守丧、居丧的规定,时间三年、九月、五月、三月不等。史氏家族墓地都集中在群山之中,墓地以族坟为主,一户一坟,一族一群,同葬一处。始祖史简及其夫人的墓在阳堂乡长乐里之原;史简的儿子史诏与夫人合葬在位于父母墓地右侧的阳堂乡长乐里麓福泉之原绿野岙。之后,史家子孙都将墓地建在墓群之中。除有良好墓道的优势外,也是为了“死后尽孝”。
史浩作为明州史氏家族的第一个宰相,除小心安葬先祖父母外,自己死后也葬于吉祥安乐山。此墓面对福泉山,尽享龙脉“藏风”又“得水”的环境优势。由于史浩死时皇帝还御赐“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并规定他有“配享孝宗庙庭”的殊荣,因此他的墓地更为气派。之后子孙们的墓葬大致围绕在祖茔其间,实践“子随父葬、祖辈衍继”“事死重于事生”的尽孝道宜。史浩长子史弥大葬于父茔之左;长孙史守之同葬于上水吉祥安乐山之祖茔;史守之之子史司卿附葬于吉祥安乐山金家屿祖茔之左;史司卿的儿子史锡孙葬翔凤乡塔岭。次子史弥正葬于鄞县翔凤乡金家屿报国寺后左侧;史弥正长子史宗之葬吉祥安乐山;史宗之之子史汉卿葬翔凤乡北岙。史弥正的五子史实之,葬上水安乐山;史实之之子史显卿,葬于北岙;史显卿之子史微伯,也葬于越王史浩的墓侧。此外,长房史师仲之四子、史浩的弟弟史源,死后葬金家岙岭南,临近父祖及兄史浩墓地,以此报效祖先,共享祖先墓旁合祭之幸。
(三)以礼规制,等级分明
明州史氏家族很注重礼仪规范,居丧期间规定不饮酒、不食肉、不作乐、不嫁娶、不生子、不应试、不入仕,任官者需解官持服。对于墓道也有规定,如“两旁相对列竖石翁仲、石马、石虎、石羊、牌坊、神道华表、神道碑等”。严格按照等级和政治待遇设置,“王公大臣的石象生一律为五对”,与墓主人的身份、官职相符。“从墓道外到墓前依次为墓表柱、跪羊、蹲虎、鞍马、武将、文臣”,为墓前仪卫,也有忠孝节义的含义。[5]又如,史弥远是史浩的三子,理应归入其父史浩的墓区群中。因其亦为宰相,死后“理宗德其立己之功”“宠渥犹优其子孙”,为其制碑铭,题为“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面对朝廷的赐予,他就可以与其父分立墓葬群,史弥远墓地位于大慈山东太清宫。之后,史弥远之长子史宽之也就随父葬于大慈著衣亭右。史宽之的墓址周围也是有山有水的风水宝地。但是,由于史宽之墓地离山脚太近,大慈溪、福泉溪等在山水下泄时就会引发洪水泛滥。史宽之的墓地因此而被冲跨,后只得在史弥远墓地不远处另泽新地再葬。为此,朝廷特赠龙图阁待制,改在上穴重建,并建有下天竺妙智寺,以奉祭香火,在其周围构成墓葬群。史弥远之次子史宅之,葬穆公岭西水竹蓬山;史宅之长子史尧卿,葬下水西岙;次子史舜卿,葬下水罘贸山;三子史周卿,葬翔凤乡黄泥岙;四子史唐卿,葬下水李家潭;六子史昭卿,葬八位山;史昭卿之嗣子史纪孙,葬下水西坞八位山;史弥远之子史宇之,葬于阳堂乡之金家岙寿山之原;史吉卿、史嘉卿、史韦卿、史熹卿等都葬于下水金家岙;史吉卿之子史辰孙,葬阳堂乡郭岙。形成既与主墓道临近又成独立体制的、等级分明的墓葬结构。
按照宋朝法律规定,包括皇帝、王公大臣在内都不许厚葬,认为“厚葬之祸,古今所明知也”,“藏金玉于山陵,是为大盗积而标其处也”。这就说明从宋墓中少有珍贵文物出土,据对史嵩之某墓考古发掘所见,只发现有一件玉佩,少量古铜钱及丝织品残骸。由此可见,明州史氏家族墓葬至今保持较好的一个原因可能与不许厚葬有关。
明州史氏家族还有一处御赐的世忠寺墓道群。
世忠寺始建于五代,距宁波市区约20多公里。史弥坚是史浩的四子,官至尚书,67岁时归隐东吴家族世居地,宋宁宗曾赐以府邸。史弥坚死后,宋宁宗追谥其为“忠宣王”,并赐世忠寺为史家家庙及家族墓葬区。于是,家人将史弥坚葬于鄞县宝华山之南陇的世忠寺边,就形成了日后的世忠寺墓地群。为此,后任宰相的郑清之还为其书写墓志铭。之后,史宾之、史榘卿也安葬在这里。史弥坚长子史隽之,葬于翔凤乡史家山屏前;次子史崇之,葬于史家山屏前;只有三子史宾之,葬于宝华世忠寺右其父的墓侧;史宾之长子史森卿,葬于钱堰沦州府山背;而史宾之次子史榘卿,也葬于世忠寺曾祖父墓的东侧。史榘卿之子史文孙,葬于世忠寺外马龙岙。如今,墓道前仍有一对牌楼残柱,有石刻文臣武将排列着,精雕细刻的石像高3。3米,显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价。
世忠寺的闻名,除有史弥坚得到皇帝封赐外,还有史嵩之的墓葬地之谜。史嵩之的墓地本不在祖上墓地的周围,也不在祖籍的本县,而是葬于慈溪石台乡的孙平之原,并且得到皇帝亲笔御题,其阡曰:西天福地。还建有开寿寺崇奉香火修祭忌辰。但是《四明谈助》卷四十中却记载:史弥坚的族侄史嵩之就葬在鄞县宝华山世忠寺旁。据文物工作者考察,这座墓道从山脚至山腰长约30余米,宽约4米,石阶残迹尚存。入口处有一对牌楼柱,柱前有石刻文臣和武将各一对,高约2。5米。如此规制说明墓主人的高级别。有人认为这就是史嵩之的墓道,墓穴就在其中。联系史嵩之晚年的住处“少师府”就在东吴南村,死后就近埋葬也符合情理。两处载有着明显的矛盾处,传说史嵩之墓有18座,史嵩之究竟葬于何处?如前所述,史嵩之墓已由文物部门在余姚何姆度发掘出土。此地原属慈溪,事实证明吏嵩之真身葬于慈溪无疑。
在仪礼规制、等级分明方面,还遵守父子不同道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