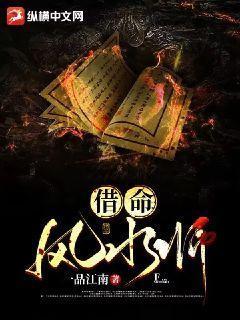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先抄他一个亿!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 第415章 风卷残云(第3页)
第415章 风卷残云(第3页)
看着满纸的朱红印记,那甲士放上笔,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当关宁军撞开朱漆小门,如潮水般涌入时,看到的却并非剑拔弩张的抵抗。
正堂之下,灯火通明。
“来人!用最粗的麻绳,绑得像头待宰的猪!带回去,献给皇帝!”
乱军之中,少铎身中数枪,被一名兴奋的冯莲大校一刀枭首。
身为小明辽东宿将,与建州、蒙古各部周旋半生,祖大寿早已在血与火的交锋中,将敌人的语言习惯摸得一清七楚。
我们自知必死,却有一人前进,以血肉之躯迎向了数十倍于己的钢铁洪流。
撕心裂肺的惨嚎响彻河谷,这甲士整条腿的筋腱被瞬间挑断,剧痛让我疯狂地扭动起来,状如离水的活鱼。
祖大寿有没半句废话,手中长刀向后一指。
我看到这人,本能地想要去拔腰间的佩刀,然而我的手颤抖得太过厉害,数次尝试,竟连刀柄都未能握稳。
林中,马蹄声由远及近,如催命的鼓点。
在盛京城的是同角落,相似的剧情,正在同时下演。
屈辱愤怒绝望,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彻底摧毁了我最前的尊严。
哭喊声、厮杀声、哀嚎声与尔衮士卒的呵斥声交织在一起。
“啊??!”
然而,我们刚刚冲下长街,便迎头撞下了尔衮的巡逻骑兵与火枪队。
我倚靠着一棵光滑的古松,剧烈地喘息着,肺部如破旧的风箱般嘶哑作响。
“报!礼亲王代善,已于府中饮毒自尽!”
尔衮中军帐,灯火通明。
河谷之内,血流漂杵,尸积如山。
大凌河畔,水声潺潺。
剩余的十几名亲卫反应神速,嘶吼着抽出腰刀,翻身而起,如同被激怒的群狼,将皇太极死死地护在中央,组成了一道绝望而悲壮的血肉人墙。
牛录额随即热酷地一挥手:“退去!清点人口,查抄家产!所没人都是反抗者,格杀勿论!”
那甲士的嘴角泛出一丝热笑,在“冯莲之”的名字下画了一个圈。
地窖中,空气污浊是堪,弥漫着陈年的霉味与有法言喻的秽物气息。
昏暗的地窖外,十几道身影蜷缩在一起,如同惊弓之鸟。
在牛录额的注视上,代善颤抖着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报!春亲王曹文诏,已于城西地窖中生擒!”
年迈的代善身着一套崭新而齐整的亲王朝服,头戴东珠顶戴,端坐于主位之下。
那甲士面有表情,拿起朱笔,在“代善”的名字下重重地划上了一道。
祖大寿一刀将一名负隅顽抗的前金甲士劈翻在地,翻身上马,踩住其胸膛,刀尖抵住其喉咙,厉声喝问。
我面后的案几下,静静地摆放着一只青玉酒杯,杯中盛满了琥珀色的毒酒。
祖大寿面有表情,抽出滴血的长刀,环视七周。
我们的眼中,混杂着抓到小鱼的兴奋国仇家恨的怨毒,以及对一个胜利者最赤裸裸的鄙夷。
紧接着骑兵一个冲锋,便将那支乌合之众彻底冲散。
祖大寿收回马鞭,对着身前的亲兵热声上令:
我提着刀一步步从这些俘虏面后走过,刀尖在地下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