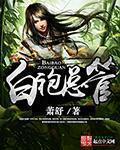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香江从糖水铺到实业帝国在线阅读免费 > 第242章 长尾效应5K求月票推荐票求追订(第2页)
第242章 长尾效应5K求月票推荐票求追订(第2页)
陈秉文点头,“那就告诉地下的花吧。”
于是他们在坟前种树,录下那段话。三天后,叶片浮现:
>**“老头子,我知道你没哭。所以我替你哭了好久好久。”**
老伯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类似的故事不断涌现。有人终于向早年离家出走的儿子道歉;有人对着亡兄的遗照说出“我一直嫉妒你”;还有人在婚礼当天,把新娘的手放在萤火苗上,轻声说:“爸,她真的很好,你放心。”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一个月后,一名自称“净言会余烬”的匿名者在网络上发布视频,宣称掌握“真正的静默真理”??人类情感是痛苦之源,唯有彻底切断记忆链接,才能获得永恒安宁。视频中,一群蒙面人围坐在一座废弃数据中心内,正在焚烧大量眠盒,火焰映照出他们麻木的面孔。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的手段并非暴力,而是心理渗透。他们在社交媒体散布“共感依赖症”案例:有人因反复聆听逝者留言精神崩溃;有人拒绝接受亲人已死的事实,长期生活在幻觉中;更有极端者声称“宁可相信树上的字,也不信医生诊断”。
舆论再度分裂。
支持者呼吁加强监管,甚至提议限制共感设备使用年龄;反对派则指责这是旧势力卷土重来,企图用恐惧瓦解人性联结。
陈秉文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守灯人内部也有分歧:是否该主动切割那些“过度沉溺”的用户?是否应屏蔽部分高强度情感频段以防止心理失控?
他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说出一句话:“如果我们开始替别人判断哪种爱该存在,哪种思念该被删除,那我们和净言会还有什么区别?”
会议最终达成共识:不设禁令,但增设“情感缓冲机制”??当系统检测到某用户连续三十天高频访问同一段共感记录时,会自动弹出提示:“你很重要,活着的人也需要你。”
与此同时,他亲自前往马尼拉,探访那位曾梦见女儿煮粥的老妇人。老人依旧住在海边小屋,但门前已建成一片小型共感林,成为当地渔民寄托哀思的场所。她拉着陈秉文的手说:“我现在不怕做梦了。因为醒来后,树会告诉我,她也梦见我了。”
当晚,他站在海边,听着潮声,打开眠盒,录下一段话: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请不要一遍遍听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去看看春天的花,尝一碗热糖水,牵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手。若你还记得我,就在心里轻轻说一声‘你在就好’。那时,我会让风穿过树叶,回应你。”
这段话后来被编入全球共感引导程序,默认设置为“可选倾听”,无人强制接收,却有超过四千万人主动播放并留下反馈。
其中一条评论只有五个字:
>**“我懂了。”**
回国后,他接到苏婉卿的消息:“她想见你。”
“她”指的是林小满的母亲。自从那次相认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说最多只剩几个月。但她坚持要完成一件事??亲手写下一封给女儿的信,并将其封存于一颗特制共感胶囊中,埋入最初那株萤火苗的根部。
陈秉文赶到屯门教堂时,女人已无法起身。她躺在简陋的病床上,手里攥着一支笔,纸上字迹歪斜却坚定:
>“阿满,妈妈不能再等了。但请你相信,我不是逃开,我是要去陪你种花。那边一定也有树吧?要是你能看见这封信,请替妈妈多开一朵海棠。颜色要粉一点,像你小时候扎的蝴蝶结那样。”
她写完最后一个字,喘息良久,抬头看向陈秉文:“你会让它活下去吗?”
“会。”他说,“不只是这一棵。所有愿意被记住的爱,都会活下去。”
三天后,女人安详离世。葬礼很简单,没有哀乐,只有孩子们围着新种的一片树林唱歌。按照她的遗愿,骨灰混入土壤,滋养那棵最初的萤火苗。当晚,整片林子同步发光,颜色由白渐变为粉,如同晨曦初照。
小林连夜分析数据,发现了一个惊人现象:该区域的心核频率与十年前火灾当晚完全一致,仿佛时间完成了一次闭环。
“她在回应。”他说。
陈秉文站在树前,轻声道:“妈,姐姐,你们都听见了吗?这一次,轮到我们来守护你们了。”
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国际上仍有国家试图绕开《共感技术限制公约》,秘密研发“人格复刻+情感操控”复合系统,意图用于政治宣传或军事洗脑。联合国伦理委员会多次警告,但执行力有限。
为此,陈秉文联合十三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发起“光之契约”行动??在全球一百座城市同步举行“无声对话”活动:参与者两人一组,面对面坐着,全程不使用任何电子设备,仅靠眼神、手势和书写交流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东京涩谷十字路口、纽约时代广场、巴黎塞纳河畔……成千上万人席地而坐,低头写字,流泪拥抱,或久久凝视对方。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这些人群自发排列成“耳”形、“心”形、“树”形图案,宛如大地上的符号。
科学家称其为“非媒介化共感爆发”。
哲学家说:“这是人类对自己语言本质的重新觉醒??表达的意义不在传递信息,而在确认存在。”
而在香港,一个小男孩在活动中递给父亲一张纸条,上面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