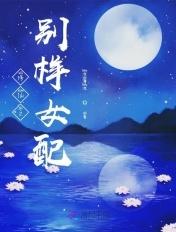奇书网>第一次石油战争 > 第3章 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第1页)
第3章 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第1页)
第3章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这种让步换来的其实就是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石油贸易,一般来讲,这种战略物资的贸易其实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条件、可以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的,可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眼中只有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长远的政治卓见,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由此彻底被埋下。
斯大林的绝地反击
石油既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所在,又是国际政治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筹码。在前苏联的历史上,自从石油的重要性被人们认识后,这种黑色**在其外交战略中就一直起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
近代以来,欧洲地缘战略的主线其实就是英国和沙俄间的争斗。当时,英国把开始崛起的沙俄当成了主要的遏制对象,俄罗斯几次向中亚、南亚及中东的战略扩张,都被英国人挡了下来;为了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英国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英国完全站在了日本一边。
但英国对待俄国的态度在“一战”前却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油在工业领域的价值已经显现了出来,英国是不产石油的,相对于进口美国和墨西哥的石油,从俄国进口石油的价格更低,且有利于分散潜在风险。
那个时候英国还明显地感觉到另外一个威胁。当时在中东地区的巴格达和波斯的西北部也已经勘探到了石油。位于欧洲中部的另一个新兴大国德国很快把目光投向了那里。德国提出巴格达铁路的战略构想:从柏林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伊斯坦布尔直达巴格达,修建一条铁路,由此建立只属于德国人的石油大动脉,这条路径如果最终实现的话,那么英国人对海洋的统治就将失去意义。此时,英国既需要石油,也需要有一支力量可以制衡德国,从这两方面考虑,英国开始减少与沙俄的冲突,最后双方在一战爆发前达成了合作关系。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把西方在俄的资产全部收归国有。1922年,曾经控制巴库油田的诺贝尔家族联合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英国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等西方资本结成联合阵线,开始向苏维埃政权施压,要求对他们被收归国有的资产进行赔偿。
当时苏联百废待兴,急需从国外引进各种技术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只能从欧洲获得,所以西方资本集团的压力绝对不容小觑。最终,还是手中的石油资源帮助苏联政府瓦解了这次攻势。苏联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外贸兼交通部长克拉辛提出:可以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许经营权的新政策,其中包括租让巴库和格罗兹尼各四分之一的油田,这个比例可以保证对方获益,但绝对拿不到控制权;此外,愿意和苏联政府合作的西方企业,可以继续从苏联进口到低价的石油。当时苏联急需外汇用于国家贸易支付,且当时其国内的工业能力根本消化不了这些石油产能,所以即便是低价出售,也还是能解决大问题。这个政策一经推出,由诺贝尔家族和皇家壳牌等形成的资本家同盟在几天之内就宣告破裂,原本准备向苏联逼债的西方资本家都急于尽快和苏联政府展开单独谈判。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在苏联对外战略方面的权重进一步增大了。我们首先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对世界新格局的构想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其实有很大的出入。美国的想法是把欧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势力彻底清除,同时,希望苏联能够在美国主导的格局当中做一个比较听话的“老二”,这就是所谓的“苏美共治”最初的由来。
为了诱使斯大林接受这个构想,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事实上都站在了苏联这一边。其中包括同意苏联把所有东欧国家纳入它自己的战略体系当中,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斯大林在接受美国所给予的这些好处的同时,却没有被这些眼前利益冲昏头脑——以苏联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它所具备的资源来说,即便美苏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差异,长远来讲苏联这个老二的位置也是坐不稳的,一旦接受了美国的安排,也就等于把国家前途一半的主导权交到了别人手里。与其如此,倒不如分庭抗礼,这样反倒会使苏联获得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成为继英国之后又一个全球的主宰者。
所以在“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已经逐步意识到苏联不会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在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苏政策中遏制的味道开始越来越明显。而斯大林则针锋相对地建立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对西方国家完全封闭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世界。
政治上,在苏联的主导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起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翻版。通过这个组织,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政府与苏共在政治口径上实现了高度的一致,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超大号的共和制国家;而与之对应的,美国与西欧所组成的资本主义阵营则更像是由一个个城邦所组成的松散的邦联——虽然美欧手中握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工业生产能力,可是由于内部实力分散,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们反倒居于下风。
在军事上,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北约;苏联则针锋相对地在1955年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在经济上,“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出了向欧洲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欧洲贷款,以此来左右欧洲的外交政策,甚至是国家经济规划的制定。斯大林非常清楚,如果东欧国家加入美国的框架,那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根本立不住,所以苏联极力阻止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解决东欧盟国的经济问题,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推出了自己的莫洛托夫计划——由苏联向遭受战争破坏的东欧国家派出技术人员,输出设备并提供贷款。
而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取消了国家界线的超大型计划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各个国家都得到了自己的分工,比如说波兰在当时主要负责农业,东德由于制造业的传统成为整个互助委员会当中重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经济互助委员会能够顺利成型,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苏联手中的石油资源。自经互会成立之后,苏联一直以低于国际价格的标准向东欧提供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使得后者的经济运行成本被大大降低。
这里顺便说下同一时期的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轻易控制欧洲,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石油。一方面,如果当时西欧国家手里没有美元就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由于罗马尼亚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西欧本土几乎再找不到像样的石油产区,而此时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已经全部丢失,其中包括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这样一来,欧洲在能源上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中东的石油已经完全被美国资本掌握起来。由此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资金循环:
西欧首先要获得美元贷款,然后用美元在中东购买石油以及石化设备,而作为附加条件,所有贷款只能用来购买美国人指定的工业设备,等于说马歇尔提供的援助绕了一圈之后,还是回到了美国资本家手里。这样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在战后能够在西方世界居于统治地位,所倚重的一个是核垄断——美国是第一个搞出原子弹的国家;一个是货币垄断——美元是当时和黄金等同的国际交换货币;第三个就是石油垄断。
苏联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也搞出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大量的油田在恢复之后开始向东欧廉价输送石油,则打破了美国对石油的垄断,使得东欧国家避免了被美国所主导的美元体系所控制,可以说其意义不亚于打破美国的核垄断。
饮鸩止渴的“攘内安外”策略
到了1949年,苏联的外围环境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当时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最大的一个由共产党主政的国家,并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1949年中国建国初期,斯大林还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也简单:近代以来,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的国民党政权,他们治理下的中国都是处于一种松散、无力的状态,所以对于新生的中国政权,苏联自然会抱以怀疑的眼光,当然,1949年苏联依然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真正让苏联意识到自己这个邻居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国土没有解放,原本就孱弱不堪的工业体系也被破坏殆尽,即便是已经解放的区域,也依然有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志愿军却能够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打到三八线以南。这一点让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这个中国和1840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府治下的中国都不一样。
由此,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支持并非仅仅是作为对朝鲜战争的回报——国与国之间原本也不存在“施恩”“报恩”这样的概念。从地缘战略上考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彻底改变战后的世界格局,而这个改变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对苏联是极其有利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曾这么描述:“‘中苏集团’是自成吉思汗之后世界上出现的控制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帝国’。”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6亿以上(建国时我国人口约4亿),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苏联来说,中国复杂的地形构造将解除其远东地区的后顾之忧,同时借助与中国的合作,苏联缺少出海口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而对中国而言,则可以从苏联获得大量的工业方面的援助,对于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而言,其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中苏同盟形成后,其影响力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说仗是中国打的,但是借助朝鲜战争,苏联在和美国的全球斗争中有了更多的底气,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频频使用否决权,被戏称为“NO先生”。在当时,苏联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中国的支持同样是非常实在的。为了恢复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苏联代表曾经长期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段时期,西方媒体眼中的中苏同盟是始终铁板一块。
在这种态势下,西方国家在心理上曾一度居于下风。由于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胀的问题,工人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西方各国在当时都存在同情甚至支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最终导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全美都在疯狂地抓“共产党特务”。
虽然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个平手,但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一次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波及到了普通人。在加利福尼亚这些太平洋沿岸的美国各州,当地的社区都成立了巡防队,一堆老头老太太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海边拿着望远镜看太平洋,随时防备有“苏联或是中国的战斗机”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中苏同盟在50年代初期十分牢固,这使得很多人相信未来世界格局的主导权将属于东方。然而好景不长,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是这些改变,使得苏联的外部环境由巅峰状态一下子开始急转直下: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说苏美之间的各种对抗依旧没有间断——譬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但就整体形势而言,赫鲁晓夫其实更倾向于接受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美苏共治”的构想。这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己主观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联的内政问题。
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做过苏军的政委,但归根到底他依旧是出身于文官集团,而他的支持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个集团。苏联政治生态的一大特点是,军方和情报部门在政治上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由军方和情报部门所组成的强力部门,是一个和文官集团对等的权力集团,强力机关和文官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显然文官集团的权重开始增加了。从文官集团角度考虑,他们其实不希望有任何对外用兵行为发生,因为一旦爆发军事冲突,那就意味着在苏联的政治体系当中,原本就有很大发言权的军方和情报机构会进一步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压制军方最好的方式是不打仗,而在美苏对抗了几年之后,如果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苏联就需要拿出一份见面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赫鲁晓夫拿出的见面礼是中国——他准备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礼物换取他想象中的美苏共治。
为了“配合”自己的新战略,苏联开始要求中国放弃核武器研制,这就是在拿中国的利益来取悦美国;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边境冲突,当时苏联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一边倒地“谴责”中国;1963年苏联和美国共同通过了《部分禁止核武器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试验,签署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企图利用国际压力封死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实力,尚无法完成地下核试验。对比5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口径高度一致就可知道,这时两个国家的裂痕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
1964年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内部斗争中失败,他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成为了新的苏共领导核心,但中苏关系对比赫鲁晓夫时代并没有本质改变,勃列日涅夫集团只不过是把赫鲁晓夫时代的激进做法变得相对保守了,他们还是以文官利益为核心的官僚集团。
中苏反目使得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了,以前的互惠互利变成了互相伤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于中国来讲,不但失去了工业、国防及外交领域强有力的外援,昔日的盟友还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因为这个威胁逼着中国搞起三线建设,把很多工业设施向西北、西南转移,比如现在在成都和贵州的飞机航空集团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苏联同样没有在对抗中得到什么好处,远东地区距离作为苏联核心区的欧洲部分非常遥远,当地人口稀少,工业基础薄弱,在这样一个地方长期保持大规模的驻军,对苏联而言无疑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这个变化是灾难性的。因为中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老大”“老二”,如果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责、展开了骂战,那么下面其他的兄弟国家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出现了分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成了亲苏派,阿尔巴尼亚成了亲华派,其余国家则选择保持中立,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觉得跟着哪一边都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拉个大旗搞不结盟运动去了。不止如此,随着中苏分裂,西方国家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野的共产党也开始了内部争论,最后导致分裂,比如印度共产党就是在中苏分裂之后引起论战,最终一分为三。
对于中国来讲,中苏分裂使得中国后面的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虽然说我们的实力远小于苏联,但毛泽东依然是以一种全球眼光来看待中苏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布局,就是从美国、日本、伊朗、土耳其一直到西欧,形成一条统一战线,我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就是对苏联进行的一个新月形包围,这样一来中国就以相对较弱的实力达到了以巧破千斤的效果。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战略,在中苏分裂之后开始出现变化。中国对一些偏右翼的保守政权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甚至一度和他们成了友好的国家——比如伊朗的巴列维、扎伊尔的蒙伯托。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中苏分裂的产物,这就是大庆油田。中苏分裂之后,如果中国无法打破石油垄断,那么势必会被俄国人捏住命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一种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坚韧毅力,在东北打出了第一口油井,解决了当时的能源问题。这不仅仅是对民族尊严,更是对整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最大限度的保护。
苏联在斯大林后时代的种种转变对于其外部环境的破坏还不仅仅限于中苏同盟。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旨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举动导致各国共产党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其实更像是一种商业上的互利,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不太牢固,但是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对抗;而社会主义的阵营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把各个国家聚拢在一起,在意识形态得到所有国家、所有人认同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往往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合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年代中苏同盟始终是压着美国打的。可是在斯大林被彻底否定后,原本的思想轴心一下子消失了,而新的领导集体中再也找不出分量相近的人物和思想,从党员干部一直到知识分子、平民因此一下子都变得无所适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思想纷纷开始兴起,思想领域开始陷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