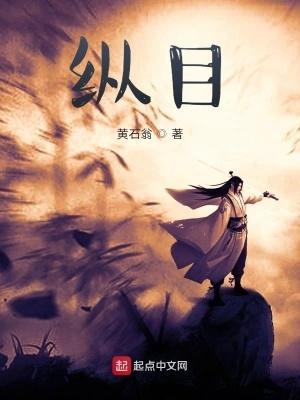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在印度看印度在线阅读 > 第七章 甘地与印度(第1页)
第七章 甘地与印度(第1页)
第七章甘地与印度
1948年1月30日那天,甘地在德里参加一场晚祷会,抵达会场走向祈祷台时,一位名叫南度蓝姆·高德西(NathuramVinayakGodse)的青年在现场真心地祝福了甘地,恭敬地向他鞠躬,然后拔出手枪近距离对着甘地的胸口连开三枪。甘地喃喃地说了最后的遗言:“哦,罗摩神!”(1)同时用手触碰额头表示为凶手祝福,随即倒在血泊中。
这种凶手与受害者相互祝福的魔幻场景,恐怕只会在印度出现。
高德西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婆罗门家庭,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他其实是一个跟甘地有着非常相似理念的人——两人都主张在印度建立统一的国家;两人都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禁欲主义等生活准则方面高度相似。
高德西跟甘地的分歧,是在关于“暴力”这个问题上。高德西认为,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证明了印度教对合法暴力的支持。《薄伽梵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最重要的一部分,般度五子之一的阿周那(Arjuna)(2)在俱卢之战前非常纠结和困惑,因为他看到许多亲朋好友都在敌对阵营里,对战争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当时化身为他的车夫的黑天(Krishna)(3)就劝导阿周那:战场只杀死肉体,杀不死灵魂,与敌人战斗是刹帝利与生俱来的责任,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信仰。
甘地则认为,从根本的出发点上,对战争暴行的反思才是《薄伽梵歌》的主旨,一切形式的暴力都应该被禁止,暴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在高德西等一些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眼里,甘地必须死。高德西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后悔。
其实,高德西与甘地并没有个人恩怨,相反他还十分崇敬作为宗教圣人的甘地;他痛恨的是甘地的“非暴力”信念,为了印度整个国家的未来,他必须杀死甘地。高德西完成刺杀后,立马就大声呼唤警察来逮捕自己。更魔幻的是,刺杀案在审理过程中,现场观众都被高德西自我牺牲的民族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甚至连甘地的两个儿子都为高德西求情,当时的法官科斯拉(GopalKhosla)后来表示:“如果让这些观众组成陪审团,并负责对高德西的上诉做出裁决的话,他们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判决被告无罪。”
但高德西还是被处死了。如果高德西不死,那就证明甘地的信念错了,会动摇整个国家对甘地的信仰。高德西杀死甘地,更加增添了甘地的传奇色彩;杀死了高德西,却也使高德西成了印度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英雄。
甘地的一生致力于发现和追求真理,梵语中的“真理”即为佛教中的“谛”(Satya)。甘地通过格“经”致知——格的是《奥义书》等宗教经典。甘地也认为万物皆有“理”,神即真理(GodisTurth),真理即神(TurthisGod),不信神的人则无缘于真理。尼采宣布“上帝已死”(Gottisttot)——神不再是生命的意义或道德的准则,人类终于从宗教道德中解放了出来;甘地却要让神作为真理和道德的形式死而复生。甘地进而创造了一个词叫作“Satyagraha”,即坚持真理,用这个口号来鼓励大家执行“非暴力”,认为只有“非暴力”才能找得到真理。
怎样通过“非暴力”来寻找真理呢?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甘地说,假如他是犹太人的话,他就开开心心地引颈就戮,自愿接受这种苦难,这样就可以带来内心的力量和欢乐,反正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因此,假如犹太人都能够在思想上为自愿受苦做好准备,即使是大屠杀,也能变成感恩和快乐的一天。(4)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甘地的这套理论跟特蕾莎修女特别像,但甘地生活的年代更早于特蕾莎修女,因此我才怀疑特蕾莎修女来到印度之后,无论是不是潜移默化,都受到甘地思想非常大的影响。特蕾莎修女把低种姓的吠舍称为“主的儿女”,而甘地在更早的时候曾把贱民称为“毗湿奴之子”(Harijan)(5)。
“非暴力”思想的核心就是,只有消灭了害怕受苦受难这种“人欲”,才能趋近“宇宙真理”——这跟特蕾莎修女对苦难的观点如出一辙。
甘地根据《奥义书》总结出一些可以让人趋近真理的行为准则,除了非暴力之外,还包括诚实、不偷不抢、劳动、节欲、禁酒、虔诚……大家看这种定义跟特蕾莎修女对“贫穷”的定义多么相似。不过,有一条例外——“Swadeshi”(6)。然而这个民族独立运动结合“非暴力”的主张,在具体实践的时候被解释成避免使用外国产品,只使用印度制造(7)。根据前后逻辑推理可得——作为印度人,你只要不用外国产品,你就是在追求宇宙真理。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会被作为追求真理的行为准则有其历史背景,为的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赶走英国殖民者。甘地相信,印度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现代文明发展造成的,只要退回到原始农业社会,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不仅抵制外国产品,更抵制整个西方文明。
除了民族独立运动之外,当时还有一个主张叫“Swaraj”,直译过来是“自治”。
甘地在1909年写了《印度自治》(HindSwaraj)一书,在当时的印度是一本禁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甘地认为,现代文明用机器生产的方式积累了太多的财富,这完全有悖于克制、节俭的宗教传统,会让人变得更加贪婪,处于一种半疯癫的状态;铁路极大地提高了出行效率,使得坏人做坏事的效率也变高了,而且由于那些宗教圣地变得太容易到达,会削弱人们对圣地的崇拜感与神秘感;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放纵,医院会让人更加缺乏对自己身体的关怀,令人道德堕落;而且医生每年杀害无数的实验动物,甚至进行活体解剖,这显然是无比邪恶的行为……总之,西方文明乃是万恶之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年印度民族独立和自治的诉求基于这样一些理论,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印度的不可思议了?
“Swaraj”是一个印地语单词,即自我统治(8)。“Swaraj”并非简单的自治,而是甘地设想的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机制,自我管理、自我统治、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自给自足,自我提供经济保障,摆脱一切束缚,最终让所有人解脱。“Swaraj”本质上是个乌托邦,但甘地却对其深信不疑,他的这种信念是哪里来的呢——印度神话《罗摩衍那》。
甘地在后期为了让底层民众更容易接受这类政治理念,给“Swaraj”套用了一个印度教教徒都很熟悉的词——罗摩盛世(Ramaraj),这个词代表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形态。甘地表示只要实现了“Swaraj”,“神的人间王国”——罗摩盛世就会到来。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相当于我们的四大名著。《摩诃婆罗多》有点像《荷马史诗》,晦涩难懂;《罗摩衍那》则通俗得多,我从头到尾通读过。
《罗摩衍那》的意思是“罗摩的历险故事”,童话故事背后是黑暗残酷的真相。
我先来讲一下童话版的《罗摩衍那》的梗概:
根据吠陀体系的推算,公元前87万多年前,阿逾陀(Ayodhya)(9)国王有三个妻子和四个儿子,他本想传位给长子罗摩,他的妃子要求他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婆罗多(Bharata),并将罗摩流放森林14年。由于妃子曾对国王有救命之恩,国王不得不答应。罗摩欣然接受安排,罗摩的弟弟拉克什曼(Lakshmana)也主动要求跟着他一起流亡。继位的婆罗多觉得自己德不配位,跑到森林里找罗摩,要请他回来做国王。罗摩表示一定要完成对父王的承诺,绝不能背弃誓言,婆罗多只能伤心地带着罗摩的鞋子回去,宣布自己只是暂时摄政,如果14年后罗摩不回来做国王,他就自杀。
当时有个十头魔王叫罗波那(Ravana),拐走了罗摩的妻子悉多(Sita)。罗摩在寻找悉多的过程中,帮助了猴国国王须羯哩婆(Surgriva),于是猴王须羯哩婆派哈努曼(Hanuman)寻找悉多,结果在斯里兰卡罗波那的皇宫里找到了。罗波那拒绝归还悉多,于是罗摩和猴子们一起攻打了魔王的国家。那些妖魔鬼怪发现罗摩是毗湿奴的化身,争先恐后让他杀死自己,以求得救赎。罗摩最后夺回了妻子,14年之约期满之际,回到故国接受了王位。从此整个王国的人民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史称“罗摩盛世”。
《罗摩衍那》的逻辑有点混乱,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一下。然而,我通过这个童话故事,解读出来另一个故事: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在印度北部阿逾陀这个地方,有个雅利安人王国,国王死后,王子们为了争夺王位手足相残,最后王位被婆罗多夺取,罗摩跟他的弟弟由于害怕被迫害,一起逃出了王都。之后他们获得了印度南部达罗毗荼人部落的帮助——或许南部达罗毗荼人部落正在与斯里兰卡岛上的原始部落交战,他们刚好卷入其中。总之,在十几年的流亡过程中,罗摩招兵买马攻城略地,甚至渡海远征斯里兰卡(也可能由于当时海平面较低,斯里兰卡与印度次大陆有路桥连接)。在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之后,罗摩杀回故国阿逾陀,成功逆袭夺回了王位。
印度人不修史,无史为鉴,不知兴替,很多时候把童话当史实。甘地对《奥义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深信不疑,这些宗教经典乃是甘地“探究真理”的源泉,他梦想中的罗摩盛世在书中也有描述:
人们都按照自己的种姓和阶级生活,一切事情无不依照圣洁的经典《吠陀》。
男男女女都虔诚地信奉罗摩,无论何人都有权利得到解脱。所有人都虔信宗教,没有人妄自尊大,男女老少都品德高尚,见不到奸诈狡猾。
——《罗摩功行录》(Ramas)
印度有些人不认同甘地的理念,甘地生前好友泰戈尔、印度的“宪法之父”阿姆倍伽尔博士(B。R。Ambedkar)都不赞同甘地的理念。
然而,由于甘地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传统宗教理念,颇受很多普通人的认同,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甘地的对错。把甘地捧上神坛的正是普通人,甘地的思想符合底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他们本来就被宗教精神影响了几千年,而甘地把古老的宗教结合现代政治重新诠释了一遍,对种姓制度、重男轻女等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进行了修补,赋予印度教古老传统在新时代以合理性。
甘地的思想如果搁在别的国家,肯定要出大问题,但在印度却和当地老百姓的日常观念十分契合,可谓如鱼得水。这不仅是宗教上的契合,更是民族性格上的契合。
后来我发现很多印度人的人生态度很消极,是因为他们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神扛着——结果好,那是神的旨意,自己努力与否都不重要;结果不好,也是神的旨意,自己努力与否都没有用。正是在有着这种观念的国家,“非暴力不抵抗”的主张才会有市场。
有相当一部分印度的底层人民都没什么上进心,还要为物质的匮乏找各种借口。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吃不饱饭的人,他们不觉得应该努力想办法吃饱,而是非要说“吃不饱才觉得食物好吃,吃太饱就不好吃了”,这种想法就跟甘地说“火车让人们太容易抵达圣地,从而失去虔诚”是一样的思路。在这一点上,特蕾莎修女跟甘地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