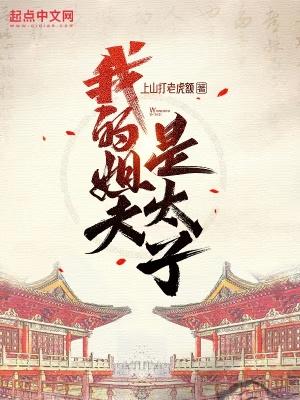奇书网>苏东坡传(上)书籍 > 三 人要有个根子(第3页)
三 人要有个根子(第3页)
海月这话说得太硬,苏轼无法回答,只能嘿嘿一笑。
眼前这位灰溜溜的才子就像一块蒙了尘土的美玉,无人擦拭,看着可惜,老和尚还是忍不住想关照他一些,略一沉吟又缓缓说道:“天竺国毘舍离城有一位维摩诘居士,是位居家的大菩萨,慧根深厚,于世间大道无不透彻明白,佛祖知道维摩诘的神通,就派文殊师利菩萨来问他佛法,两位菩萨一问一答妙语连珠,内中道理至深,引得无数菩萨、罗汉、比丘齐来听讲,至精妙处,又有龙女现于云端散下五彩花瓣。也怪,这花瓣落在菩萨们身上,有些立时滚落了,有些却沾在衣服上,那些衣服上沾了花瓣的就抖落衣袖想把花瓣掸去,哪知花瓣却粘在身上怎么也抖不掉,后来越沾越多,遍体皆是,不得不问龙女:‘他那里一叶不沾,我这里遍体都是,此为何故?’龙女答道:‘他视花瓣如无物,你视花瓣为有物,他心中无挂碍,你心中有挂碍,于是你这里略有沾着。而你有心抖落,是挂碍越重,沾连越多,此皆在你,与别人无关。’”看了苏轼一眼,见他瞪着两眼茫然若失,大概一点也没听懂,就笑着说,“你看,天上有花瓣掉下来了!”
其实天上并没有东西掉下来,可苏轼听讲听得仔细,还是下意识地把袍袖拂了几拂。海月和尚不禁笑了起来:“你也知道花瓣落下是必要沾身的,因为你心中有无穷挂碍,处处舍不得。要想知道什么是‘放下’,必先知道什么是挂碍,我且问你:你心里究竟有何挂碍?”
苏轼两眼望天想了好半晌:“我心里贪恋功名,挂碍极深。”
“施主好名吗?”
和尚一问,苏学士不得不承认:“在下好名。”
“好利吗?”
“也好利……”
“好美色吗?”
这一问倒把苏轼问笑了,略想了想,老实答道:“也好色。”
“好难得之财货吗?”
听了这话苏轼顿时想起当年凤翔府一百贯钱买回来的四面门板,这是一辈子忘不掉的教训:“也好难得之货。”
“好炫耀吗?”
“也好炫耀……”
“好口舌之争吗?”
老和尚这一问正在要害处。奇怪的是苏轼竟不肯像刚才那样轻易承认了,低头想了一会儿,这才说道:“我以为天下事当争则争,当论则论,未必都能三缄其口。”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功名、美色、财货之类苏子瞻随口承认,说明他这个人不功利、无**欲、不贪婪,可苏判官不承认他好口舌之争,恰好说明他身上的毛病就在于嗔心重,受争执。
海月和尚知道苏轼的“病根子”,也不和他争论,只笑着问:“你觉得什么事应该争论?”
“心里知道对的事就要争论。”
“心里怎么知道对错呢?”
“自然有良知在。”
“良知必是真切笃实吗?”
苏轼连想也没想,立刻答道:“良知是眼见、耳闻、心想,发于至善,毫无杂念,自然真切,不会有错。”
到这时,苏学士身上要强好胜爱争执的病根子已经露出来了,海月和尚又是微微一笑:“《大般涅槃经》里有个故事:天竺有一位国王名叫镜面王,当时举国只有他一人信奉佛法,其余人信得都是旁门左道。于是镜面王叫人牵来一头大象,让几个盲人去摸,摸到象牙的说:‘大象如同一根萝卜。’摸到象耳的人说:‘大象如同一把蒲扇。’摸到象头的人说:‘大象如同一块石头。’摸到象鼻的人说:‘大象如同一根杵。’摸到象腿的人说:‘大象如同舂米的木臼。’摸到象背的人说:‘大象如同一张床。’摸到象腹的人说:‘大象如同一只瓮。’摸到象尾的人说:‘大象如同一条绳子。’于是诸人争论不休,没有了局。请问学士,这些盲人所说的算不算‘发于至善,毫无杂念’呢?难道就因为他们说的话‘发于至善,毫无杂念’,这场稀里糊涂的争论就有意义了吗?”
被老和尚一问,苏轼又无话可说了。
海月和尚缓缓说道:“好争执是个大忌,一个‘争’字顿时引出贪、嗔、痴、慢、疑五种毒来。你想想,好争执的人怎能不贪得,不嗔怒,不愚顽,不自大,不否定旁人?于是陷入荆棘,多被刺伤,这是自己寻回来的烦恼。”
老和尚这些话极能劝人,苏子瞻又是个极灵透的人,听了这些话心里顿时起了感应,半天才问:“这么说,还是应该做个与世无争的人?”
海月和尚看了苏轼一眼,微微摇头:“话不能这样说。六祖慧能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兔子是不长角的,所以求不到。释、道、儒三教立论不同,法门却相同,都是先修身,再度人。你是个儒生,儒生学的是孔孟之道,是‘克已复礼’,这‘克已复礼’是先修炼自身,自身有了道德,再去劝谏皇帝。修炼自身是一场修行,劝阻皇帝,为民请命,更是一场极大的修行。所以为民请命是儒生的天理,良知一旦发动,为了百姓利益,心中全无杂念,这时候该争的务必去争。只是你记着:不争,事不关已;一争,便入荆棘。佛说:‘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若心动则人妄动,痛其身伤其骨,于是体会世间诸般痛苦。’然而不动心又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被荆棘刺痛之时怎么才能定住身子,脱出苦痛,归于快活,这就要有一个‘根子’,能让自己站得住才行。”
听海月大和尚说到“人要有个根子”苏轼忽然似有所悟,忙问:“以前曾有位高僧对我说过:‘无常是苦,然而苦中有一点乐,衔而游之,便见活水。’这与大师所说的‘心里的根子’是一回事吗?”
一听这话海月也笑了:“是一回事,只不过人家说得更贴切。”
“这‘根子’也好‘活水’也好,到底是什么?”
苏轼这一问,是代天下人向佛求法。海月和尚略一沉吟,缓缓说道:“是个‘自我。’世间多苦恼,皆因不识‘自我’。”
听到这里苏轼忙问:“如何寻得‘自我’?”
老和尚淡淡地说:“不可说,不可说……人生道路不同,际遇不同,见解也各不相同,到最后才知道都是一样,早先却说不得,一说就错了。这就像把树封在坛子里让它成长,还没长大已经死了。”
海月和尚这些话已经讲到高深之处,糊涂人往往越想越多,甚至陷溺其中,明白人却能适可而止。苏学士颇有慧根,倒是个明白人,暗暗点头,嘴里低声说:“原来自己的路还要自己走,‘活水’要自己去寻,衔而游之,皆是自然而然的事。”
老和尚点点头:“你能明白这些就好。晚课已毕,施主也来吃碗斋饭吧。”
与海月和尚讲论佛法,苏轼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忙说:“这碗斋饭是要吃的。”有说有笑,随着海月和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