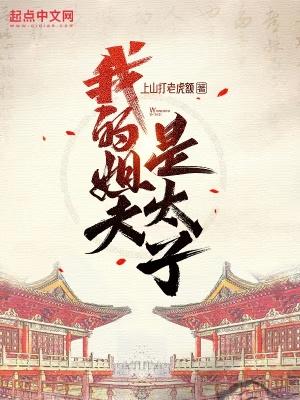奇书网>叶圣陶集pdf > 02(第4页)
02(第4页)
“今人于吃饭时,虽然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译文】
先生说:“现在,有些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他的心也经常不安定,只因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原文】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
【译文】
先生说:“琴瑟与书籍,学者不能或缺,由于常有事可做,心就不会放纵。”
【原文】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译文】
先生感叹地说:“世间知学的人,只要这些毛病不能纠正,就称不上‘善与人同’了。”
崇一接着说:“所谓的毛病,也就是因为好高骛远而不能舍己从人。”
【原文】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译文】
有人问:“良知本来是中和的,如何会有过与不及呢?”
先生说:“清楚了过与不及,也就是中和。”
【原文】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①
【注释】
①所引两语皆出自《大学》。
【译文】
先生说:“‘所恶于上’,就是良知;‘毋以使下’,就是致知。”
【原文】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译文】
先生说:“张仪、苏秦的谋略,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代的诸多事业文章,诸多的豪杰名家,只是学到了张仪、苏秦使用过的方法。张仪、苏秦的学问很会揣摩人情,没有哪一点不是切中要害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不能穷尽。张仪、苏秦已窥到了良知的妙用处,但没有把它用在点子上。”
【原文】
或问未发、已发。
先生曰:“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
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可谓无,即扣不可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即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
【译文】
有人就未发、已发的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只因后世孺者将未发、已发分开来讲了,所以我只有直接说一个没有未发、已发,让世人自己思考而有所得。若说有一个已发、未发,听讲的人依然回到后儒的见解上。若能真正认识到没有未发、已发,即使讲有未发、已发也无妨。本来就存在未发、已发。”
有人问:“未发并非不和,已发也并非不中。例如钟声,没敲不能说无,敲了也不能说有。但是,它到底有敲和不敲的分别,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没敲时原本就是惊天动地的,敲了之后也只是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