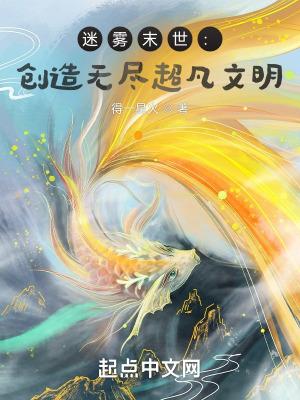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文豪1879独行法兰西无弹窗笔趣阁 > 第417章 法兰西民族的顽疾(第3页)
第417章 法兰西民族的顽疾(第3页)
>“您追求的是力量的极致,我守护的是距离的温度。或许我们并非敌人,只是站在电流的两端:您让雷电驯服于钢塔,我让微光扎根于泥土。若有一天,您的巨流能分流至每户门前,而不必强制穿越每道门槛,那便是真正胜利。”
半月后,竟收到回信。字迹潦草却真诚:
>“亲爱的托马斯:
>
>你让我想起科罗拉多山中的小屋,那里没有变压器,只有一盏煤油灯和一本尼采。伟大未必喧嚣,静默亦可深远。我会关注你的‘微光计划’。也许某天,我们可以谈谈,如何让巨流与细流共存。
>
>??Nikola”
我将信贴在实验室墙上。
年底最后一周,巴黎迎来第一场雪。
我独自步行至西郊,走访十余户家庭,检查供电情况。多数线路运行良好,少数因积雪压断,但备用储能迅速启动,平均断电时间不足七分钟。孩子们在灯下读书,老人围炉交谈,面包店凌晨三点就亮起暖黄灯光,为夜归人烘烤热餐。
这才是我要守护的世界。
圣诞夜,我受邀参加贝尔维尔教堂的烛光仪式。牧师讲道完毕,突然宣布:“今晚,我们将不用蜡烛。”
全场惊讶。
接着,所有灯光熄灭。十秒后,一盏、两盏、三盏……整座教堂的吊灯依次亮起,靠的正是我们安装的混合供电系统:潮汐+风力+人力储能。
“这不是神迹,”牧师说,“是无数双手,一点一滴,把光捧到了我们面前。”
我坐在后排,眼眶发热。
散场时,一个小女孩跑来,塞给我一张折纸。打开一看,是幅蜡笔画:一个戴礼帽的男人,手中牵着一串发光的星星,旁边写着:“谢谢你,让黑夜不再可怕。”
我小心收好。
回家路上,雪越下越大。马车载着我穿行于静谧街巷,每一盏路灯都在风雪中坚守岗位,像哨兵,像朋友,像永不放弃的诺言。
推开家门,壁炉尚有余温。我脱下湿大衣,取出日记本,写下最后一段:
>“今日方知,真正的革命不在议会厅,不在专利局,而在一个母亲敢让孩子晚归的安心里,在一位老人能独自夜行的从容中。我们争的不是电流方向,而是生活的主权。
>
>或许未来某天,所有的网终将相连。但在此之前,请允许一些地方先亮起来??不是被赐予,而是自己点燃。
>
>光,本就不该等待许可。”
合上本子,窗外雪落无声。
我知道,风暴仍在远方酝酿。爱迪生不会善罢甘休,华尔街的触角只会更深。但此刻,巴黎的灯火安稳,人间值得。
而我,仍将执笔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