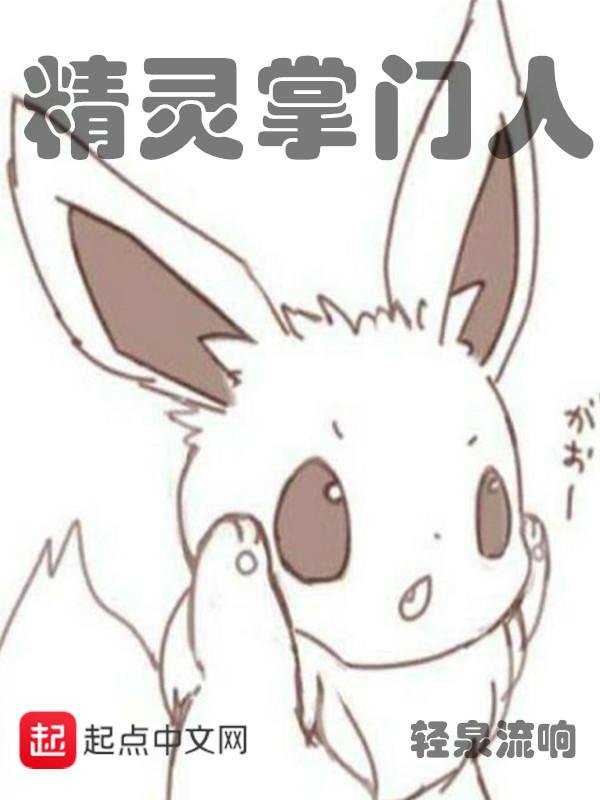奇书网>民俗从傩戏班子开始无弹窗阅读 > 第231章各自守城驱傩化灾33(第1页)
第231章各自守城驱傩化灾33(第1页)
帝国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也像是一个巨大的,不成比例的蚰蜒。
蜘蛛网上面的一点动静,震荡到了下面,那便是“排山倒海”一般的恐怖气韵,就像是现在,“方公公”回去之后,各地的矿监和税关的事情,已。。。
风卷着雪粒,在终焉之井的石沿上打转,像无数细小的手指轻轻叩击着大地的骨节。林朔坐在竹椅里,裹着厚厚的毛毯,胸口起伏微弱,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要从深渊里捞取一丝热气。他的手指枯瘦如柴,却仍下意识地摩挲着鼓面上那支稻草笛??它早已不再属于他,可触感却刻进了骨髓。
禾苗蹲在井边,用炭笔在一块桐木板上写下新的名字。她的动作很慢,每一笔都像在缝合一道看不见的伤口。木板越来越多,堆成一圈矮墙,围住那口不再沸腾却始终温润的井。有人送来纸条,有人寄来录音,有人徒步千里,只为亲手放一朵蓝莲花入水。名字从未停止生长,如同野草穿透水泥,固执地探向天空。
“今天又来了七个。”她回头对林朔说,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一个是从云南寄来的族谱残页,上面有个叫‘阿?’的女孩,十二岁那年被带走再没回来;还有一个是精神病院护工写的,说他照顾的一位老人临终前反复念叨‘我不是李二狗,我是周文远,我写过诗’……”
林朔闭着眼,嘴角微微扬起:“那就写上去。”
“可木板快满了。”她叹了口气,“我们得烧一批了。”
他点点头:“该烧了。名字不是用来堆积的,是用来唤醒的。”
于是当夜,他们在井畔燃起篝火。村民陆续赶来,每人手里捧着一块写满字迹的木板,沉默地投入火焰。火光中,那些名字扭曲、跳跃、升腾,化作黑烟融入星空。没有人哭,也没有人笑,只有风穿过人群,带着焦味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温柔。
小归站在火光最暗处,依旧是七八岁孩童的模样,星光玉笛横于臂弯,却不曾吹响。他望着跳跃的焰舌,忽然开口:“你们知道为什么火能带走名字吗?”
没人回答。
“因为火是最古老的耳朵。”他说,“在人类学会书写之前,故事都是靠篝火旁的口述流传。火焰吞噬语言,也保存语言。它把声音炼成灰,再撒回大地深处,让后来的人踩着这些灰走路时,脚底会发烫。”
禾苗怔住了。
林朔缓缓睁开眼:“所以……这火,也是傩的一部分?”
“傩从来不止是戏。”小归微笑,“它是记忆的仪式,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世界之间,唯一的通话线。你们以为你们创造了它?不,你们只是重新接通了断掉的线路。”
话音落下,火焰骤然一颤,竟在空中凝成一道人影??模糊、摇曳,却能看出是个穿蓝布衫的老妇,手里提着一盏油纸灯笼。
“妈?”禾苗猛地站起身,声音发抖。
那影子没说话,只是轻轻点头,然后指向井中。
众人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井水不知何时已变成深紫色,宛如凝固的血液。水面之下,隐约浮现出层层叠叠的台阶,向下延伸,消失在无尽黑暗之中。
“那是……归途的另一端?”有人低语。
小归摇头:“那是‘未名之阶’??所有尚未被找回的名字沉睡的地方。它们被困在那里,没有笛声指引,无法踏上桥。”
林朔挣扎着坐直身体:“那我们现在就吹。”
“不行。”小归看着他,“你已经献出了八十一场祭典的生命力,再动一次唇舌,魂就会散。”
“那怎么办?”禾苗急道,“难道任他们永远沉沦?”
小归望向四周:“那就需要更多人一起吹。不是一个人的笛,是一千个人的呼喊;不是一段旋律,是千万种声音的共振。只有这样,才能震开井底的封印。”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脚步声。
先是零星几个,接着是成群结队。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拄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婴儿的母亲,甚至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戴着手铐的囚犯、披着袈裟的僧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手中无一例外都拿着能发声的东西:口哨、铃铛、铜盆、竹梆、旧收音机……
一位盲人老太太由孙女搀扶着走近,怀里紧紧抱着一架破旧的风琴。“我爹是守语司第一批记录员,”她沙哑地说,“他偷偷抄下了三百多个名字,藏在琴箱夹层里。后来他们把他关进静音房,三天后出来时,舌头被割了。但他临死前用指甲在我掌心划了四个字??‘别忘了’。”
她说完,掀开琴盖,颤抖的手按下第一个键。
音符响起的瞬间,井水剧烈震荡,一圈圈涟漪扩散开来,如同心跳加速。紧接着,第二个人奏响了手中的铁锅,第三个人敲响了扁担,第四个人吹起了孩子丢弃的塑料哨子……
声音杂乱无章,却又奇妙地彼此呼应,像是混沌初开时的第一缕秩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节奏逐渐成型,竟自发形成了一种古老而陌生的韵律??既不像现代音乐,也不似传统民谣,倒像是大地本身在低语。
小归终于举起星光玉笛。
第一声笛音划破夜空,清冷如月光洒落雪原。
刹那间,天地俱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