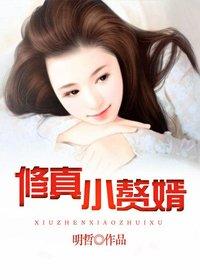奇书网>师叔你的法宝太不正经了李寒舟的身份 > 第1055章 星辰开路(第2页)
第1055章 星辰开路(第2页)
没有人劝他。
风掠过铃花,沙沙作响,像是在替他回应。
傍晚时分,阿砾独自回到山顶的共鸣阵。干枯的铃花藤蔓缠绕铜管,像一层层凝固的时间。她坐下来,轻轻哼起那首童谣。音节不高,也不美,甚至有些跑调,但她坚持唱完了一遍又一遍。
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微弱的回响??不是电子信号,不是广播传输,而是真实的、人类的声音。
一个孩子跟着哼了一句。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然后是一整片山谷的低语,如同潮水缓缓漫过岩石。
她闭上眼,听见父亲的声音在记忆深处响起:
>“语言最初不是为了传递信息,是为了证明‘我在’。”
第二天清晨,一封匿名邮件悄然抵达数百个独立媒体终端。附件是一段未经剪辑的监控录像,拍摄于某市N-12推广中心内部会议室。画面中,几位高级官员正在讨论下一阶段计划:
>“数据显示,93%的使用者在三个月内报告幸福感提升。但我们发现,仍有约6%的人表现出‘隐性抵抗’??他们按时打卡、配合评估,但在私人日记或加密通讯中频繁使用负面词汇。”
>“建议启动‘情感再校准’模块,通过梦境植入技术温和引导认知偏差。”
>“另外,对‘非共识聚集区’如山谷图书馆,考虑以‘文化扶贫’名义派驻心理辅导员,进行长期情绪干预。”
会议结束前,一人提问:
>“如果他们始终坚持‘不修复’呢?”
>镜头转向主位的男人,他端起茶杯,语气平静:
>“那就让他们成为反面教材。当所有人都‘幸福’时,痛苦本身就会变成最大的羞耻。”
这段视频没有标题,只有文件名:
>“他们害怕的,不是我们不快乐,而是我们敢于不快乐。”
它迅速在离线网络中传播,像一颗沉入深海的火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卸载N-12,或改用自制屏蔽器阻断信号。城市角落悄然出现“静默角”??废弃电话亭、地下车库、老旧电梯间,被人们改造成短暂脱离系统的情绪避难所。在里面,你可以哭泣、咒骂、发呆,甚至说出“我希望世界毁灭”这样的话,而不必担心警报响起。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原本支持“暖光工程”的专业人士也开始动摇。一位知名心理医生在学术会议上公开质疑:
>“我们是否混淆了‘心理健康’与‘情绪顺从’?当一个人不再焦虑,是因为他真正释怀,还是因为他被调成了‘默认愉悦模式’?”
>他展示了一组数据:接受N-12治疗的患者中,创造性思维测试得分平均下降18%,共情能力波动加剧,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偏好趋向单一化。
>“我们在消除痛苦的同时,也可能正在抹除人类最珍贵的多样性。”
舆论开始分裂。主流媒体仍强调“科技疗愈”的正面成果,称反对者为“情绪原教旨主义者”;但社交媒体上,#我可以不快乐#的话题悄然登上热搜,附带thousands条真实故事:
>“我抑郁症三年,现在好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世界:那段时间的痛,不是错误,是我活着的证据。”
>“我装了N-12,确实轻松了。可某天醒来,我发现我已经记不清母亲葬礼那天的心情。我开始害怕??如果连悲伤都能被删掉,那爱是不是也会消失?”
第七天,一场暴雨再次降临山谷。
雷声滚滚中,图书馆的屋顶漏了水,滴在那只新生的泥鸟身上,泥土缓缓融化,露出内里一道细小的金属丝??竟是用V-09芯片残片熔铸而成的骨架。
沈砚捡起它,怔住:“这是谁做的?”
阿砾轻轻擦去泥渍,指尖抚过那根微弱发光的线路:“是那些不愿被‘治愈’的人。他们把旧世界的碎片,做成了新生命的支撑。”
她将泥鸟放回窗台,任雨水冲刷。泥土尽去后,它不再像鸟,倒像某种未命名的生物,翅膀歪斜,眼睛空洞,却倔强地朝着天空伸展脖颈。
深夜,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麦田里,手中握着一根线,线的另一端连着千万朵铃花。风吹来,花齐摇,整个大地随之震颤。父亲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你不必改变任何人。
>你只需让那些想要真实的人,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醒来时,天光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