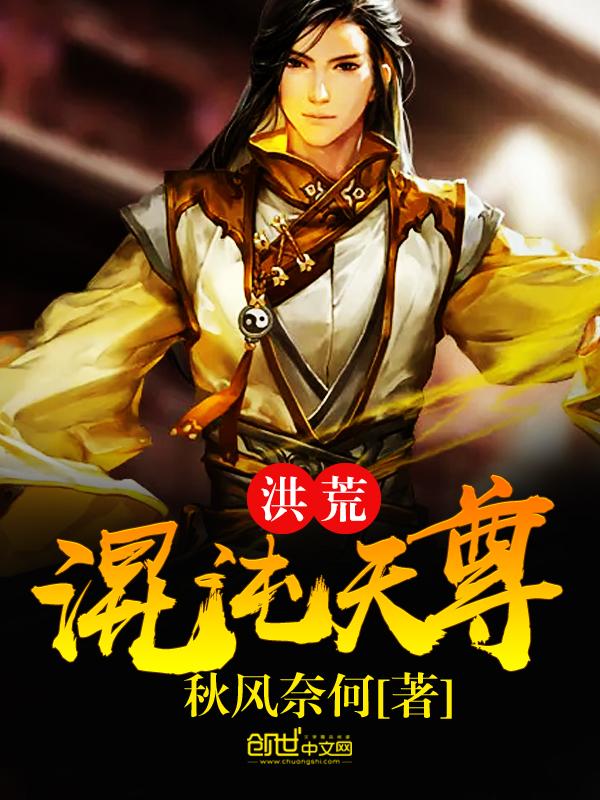奇书网>文豪1879独行法兰西作者长夜风过 > 第379章 打卡新成就(第3页)
第379章 打卡新成就(第3页)
压力之下,司法部终于正式宣布撤销对《灰烬之下》的起诉,理由是“证据不足,且不具备现实危害性”。
消息传来那天,埃米尔独自一人去了蒙马特公墓。他在一座朴素的墓碑前停下??那是他父亲的安息之地。老人一生平凡,只是一名铁路工人,临终前唯一叮嘱儿子的话是:“好好念书,将来做个能替穷人说话的人。”
他放下一束野菊,低声说:“爸,我没给您丢脸。”
冬至前夕,埃米尔完成了《灰烬之下》的最终章。他在结尾写道:
>“故事结束了,但斗争没有。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捕,
>不知道这本书还能流传多久,
>可我知道,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读,
>还有一个人敢于写,
>那么灰烬之下,终将重生火焰。
>致所有不愿沉默的灵魂:
>我们不是风暴,我们是点燃风暴的光。”
这部完整版小说通过地下渠道迅速传遍全国,甚至越过边境流入比利时与意大利。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诗人团体果然将全文抄录,制成百米长卷,在市政广场公开展出,引来数万人参观。
1880年元旦,《时代报》罕见地在头版刊登了一幅插画:一只燃烧的羽毛笔悬于巴黎上空,下方是无数仰望的脸庞。配文仅有一句:
>“有些文字,注定不属于书页,而属于历史。”
而在伦敦,萧伯纳读完译本后写信给埃米尔:“你让我明白,最锋利的革命,往往始于一句诚实的话。”
春天来临时,埃米尔受邀前往布鲁塞尔参加第一届“欧洲自由写作大会”。当他踏上火车站月台时,一群青年学生齐声朗诵《灰烬之下》的开篇词,声音汇成洪流,在晨风中激荡。
加缪笑着递给他一张车票:“去吧,别回头。这个世界需要听见更多你的声音。”
马恩站在不远处,举起手杖致意。阳光照在他银白的头发上,宛如加冕。
火车缓缓启动,埃米尔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忽然想起那个雨夜,蒙面人递出的那枚刻鹰怀表。他曾以为那是威胁的终点,现在才懂,那不过是起点。
他打开随身笔记本,写下新的日记:
>“他们用恐惧筑墙,我们用文字凿洞。
>每一次书写,都是越狱。
>而我愿终身流亡于真理之境,
>不为胜利,只为不让黑暗忘记光的模样。”
列车驶向远方,穿过田野、森林与初融的雪线。在某一节车厢里,有个少年正偷偷翻阅一本封面磨损的小说,嘴角微微扬起。
他知道,自己不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