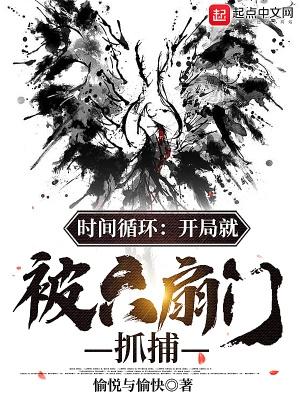奇书网>废什么太子 > 第135章(第2页)
第135章(第2页)
狄青是他的人,他打下来的战绩,都会有他的一份功劳在。
而且,狄青打仗取胜,增加的是他作为帝王的威望。
这种机会,他可不想就此错过。
只是,魏徵出于一片公心,也是为了大唐好,他也只好听着。
即便是魏徵骂他,他也只能受着。
魏徵突然踉跄扑向殿柱,袖中哗啦啦抖出度支簿:“去岁关中大旱,河东道仓廪存粮仅够三月!檄文上‘赏绢百匹’——”
枯手指向户部尚书,“敢问戚尚书,国库绢帛可够悬五百颗胡虏头颅?”满殿朱紫闻言变色,那簿册砸在地上,正翻到“灵州军械锈蚀六成”的密注。
“陛下,当真要让突厥人的血,染红陛。。。。。。太上皇‘贞观’的年号么?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陛下?陛下可还没有登基!”
“若是如此而为,恐将祸患无穷。若能胜,尚且好说,可若是败。。。。。。”
“若陛下执意要写《哀突厥赋》,老臣请先为大唐写《哭关中赋》!”
魏徵说完这些后,整个太极殿,一片死寂。
众人纷纷噤若寒蝉。
他们心中暗道:魏徵不会仗着是陛下的先生,就如此胆大妄为吧?玄武门之变还没过去多久呢?
陛下的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
这一次,陛下肯定会震怒。
这魏徵,怕是今后要离开朝堂了。
然而,年轻帝王接下来的态度,却是让众人瞠目结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李承乾面露温和,丝毫没有因为魏徵的劝谏而露出不满,反而笑道:“魏侍中言之有理,今后群臣有谏言,皆可直言,若有利于大唐,朕当采纳。魏侍中能犯颜直谏,朕忽而有些明悟。”
“众卿都可以听一听朕的一些感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以为,若是大唐能够多一些魏侍中这样的人,大唐何愁不强盛?”
“当然,朕以为对边民当以赈灾、筑城为先,解百姓之必急必忧,因为朕觉得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可不察。但——”
“与突厥和谈,并非上策。在朕之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讨突厥虽不能急于发兵而使百姓陷于战火,但若是能够一战而灭突厥呢?”
“若是就粮于敌,再遣一善战之将军,并做好边地驻防,未尝不可为?”
“不知魏侍中以为如何?诸卿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