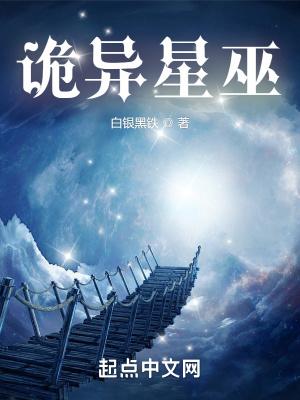奇书网>大宋文豪主角娶了几个老婆 > 第165章 抉择(第3页)
第165章 抉择(第3页)
数日后,赵元甫亲自修书一封,命人送往京师,推荐陆北顾于曾巩门下。
与此同时,张安国亦多方奔走,为其在京师谋得一席之地。
终于,在春末夏初之际,陆北顾辞别成都,启程前往京师。
临行前夜,梁娴再次来访。
“你真的决定了?”她低声问道。
陆北顾点头:“是。”
梁娴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京城不是嘉州,也不是成都。那里的人,不会因一篇文章而对你刮目相看。”
“我知道。”陆北顾淡淡一笑,“但我仍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梁娴沉默片刻,忽然取出一物递给他。
“这是什么?”陆北顾接过。
“一把剑。”梁娴轻声道,“你总说,自己像一把剑,锋芒内敛。如今,你该让它出鞘了。”
陆北顾低头看着手中短剑,剑鞘古朴,却透着寒光。
他轻轻抽出一寸,只见刃口锋利如雪,映照出他的眼神??坚定、冷静、毫无畏惧。
他缓缓将剑收回鞘中,郑重地系于腰间。
“我会带着它。”他说。
第二日清晨,陆北顾踏上赴京之路。
随行者,除了仆从,还有崔文?和周明远。他们皆自愿同行,一则为了追随陆北顾,二则也想见识真正的庙堂世界。
一路风尘仆仆,几经辗转,终至汴京。
此时的汴京,正值盛夏,繁华似锦,车马如龙。城中达官贵人往来不绝,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陆北顾一行抵达后,暂居于张安国安排的客栈之中。
翌日,曾巩亲自派人前来接引。
“曾大人请陆公子即刻前往府上相见。”来人恭敬地说道。
陆北顾整理衣冠,带上那柄短剑,步入曾府。
曾巩年约四十,身材瘦削,神情儒雅,举止温和却不失威严。他细细打量陆北顾,眼中闪过一丝欣赏。
“陆公子大名,我早有耳闻。”曾巩微笑道,“《项籍论》与《变法十策》,皆令人敬佩。”
陆北顾拱手施礼:“晚辈浅薄,不过略抒己见,还望大人指教。”
曾巩示意他坐下,随即正色道:“你的文章,我已呈予欧阳先生阅览。他对你的见解颇为赞赏,有意引荐于翰林院。”
此言一出,陆北顾心中一震。
翰林院,乃是天子近臣之所,凡入其中者,皆为当世俊才。
若能入翰林,便意味着真正踏入朝堂核心。
但他深知,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晚辈愿竭尽所能,不负所托。”他郑重答道。
曾巩满意地点点头:“很好。你既志在变革,便须先学会如何在这座庙堂中生存。”
陆北顾郑重地应声:“是。”
他知道,自己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从此之后,他不再是蜀中一介布衣,而是真正踏上了通往庙堂的道路。
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帷幕。
而他,也将在这条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