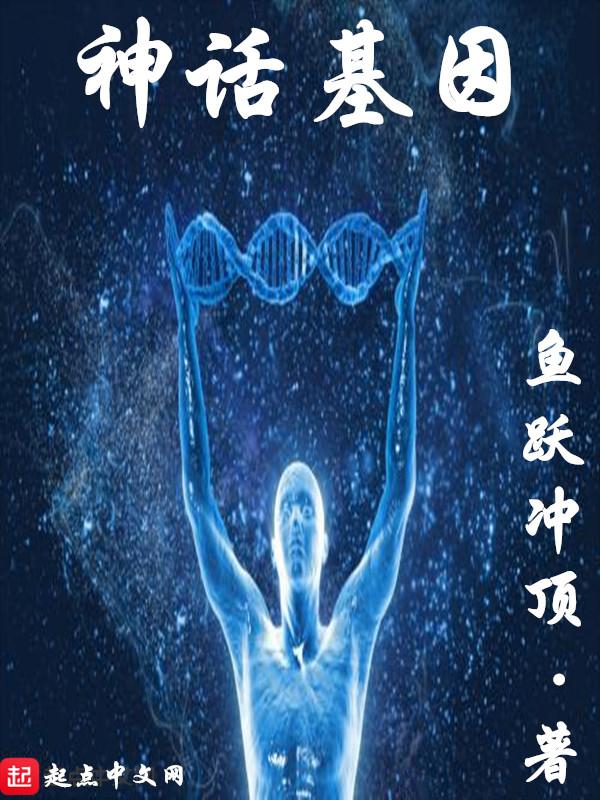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窃子疑云 > 19第 19 章(第1页)
19第 19 章(第1页)
扶观楹小声解释道:“我身子比较丰腴,胸口太过隆起不雅观,也不够端庄。”
阿清:“莫要苛待自己,妄自菲薄,不舒服就不要束了。”
“可是。。。。。。”
“不要被旁人的眼光所束缚,端庄并非是看表象。”
扶观楹顿了顿:“夫君,你先前不是让我矜持吗?若是我袒露了,我怕你说我。”
闻言,阿清怔然,未料过去和妻子说过的话会有一日反哺到自己身上。
沉默片刻,阿清淡声说:“这是两回事,矜持是指约束自身行为,不是让你束缚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扶观楹颤着眼睫:“嗯。”
和妻子谈话的工夫,好丈夫阿清没忘记继续帮妻子缓解痛苦。
“你往下一点,稍微重些。”扶观楹低低羞语。
阿清压着眉眼。
“。。。。。。呼。”扶观楹面色潮红,眼儿蕴了些泪,呼出的气息撒在他的脖颈上。
阿清面无表情,眸色平淡,好像是平静的,是不情愿的,是被迫的,仅仅是为了给妻子治病才不得已如此。
这个中滋味于他而言什么也不算。
他是在给妻子治病。
他没有半分的热衷,亦没有一点儿想入非非的绮思,像一位医术高超的妇科圣手秉承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慈悲心理,为一位饱受痛苦的年轻妇人治病。
就是这治病的法子非常奇特,但只要心智坚定,不为皮囊欲望所迷惑,便能治好病人,自己亦会安然无恙,保住神医的名声。
生病的妻子在他怀里扭动,像是热锅上的油水,噼里啪啦炸开。
妻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体温却透过布料渗出,每一次吸气几欲要把胸口的衣裳撑破。
二人肢体厮磨,缠得他动弹不得,阿清闭上眼睛。
“勿要乱动。”阿清提醒道。
扶观楹扯住他的衣襟:“我没乱动。”
阿清扣住妻子柔软纤细的腰肢,感受她因他而起的战栗,忽然想也不怪妻子会如此,她的身段妖娆,乍一看着实算不上端庄。
“另一边。。。。。。”扶观楹弱声,在他耳边不吝于妖精在蛊惑他犯戒。
阿清睁开眼,又闭上,如此反复几个来回,继续给生病的妻子治病。
从生涩到熟练。
他隐忍着,嘴唇无声默念昔日给扶观楹读过的圣贤道理。
扶观楹喘息着,控制不住要溢出声音来。
这场勾引扶观楹以身入局,面对男人的抚摸,她怎么可能没有反应?
扶观楹告诉自己这很正常,她是个正常人,有欲望乃人之常情,被男人碰触,又知过人事,所以。。。。。。在所难免。
可扶观楹害怕自己溢出声来,因为一旦溢出声音就会暴露她也沉浸在这场勾引的戏码内,她内心是渴望的,是放荡的,也有着蓬勃的欲望,只从前被自己忽视压抑了。
她觉得自己疯了,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这种女人,放浪形骸。
她对不起玉珩之,愧疚之心达到顶峰。
扶观楹又安慰自己,这是必然的,倘若她不下猛药勾引太子,太子不会碰她。
杂乱不堪的念头被强行摁下去。
扶观楹的狐狸眼漫上雾气,极需要什么塞住不受控制的嘴,于是她咬住阿清的衣料,不多时那块衣料就被扶观楹的涎水打湿。
寂静的卧房里,只听得到两人的呼吸声。
许久之后,阿清道:“可好些了?”
扶观楹觉得够了:“嗯,谢谢夫君。”
声音羞涩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