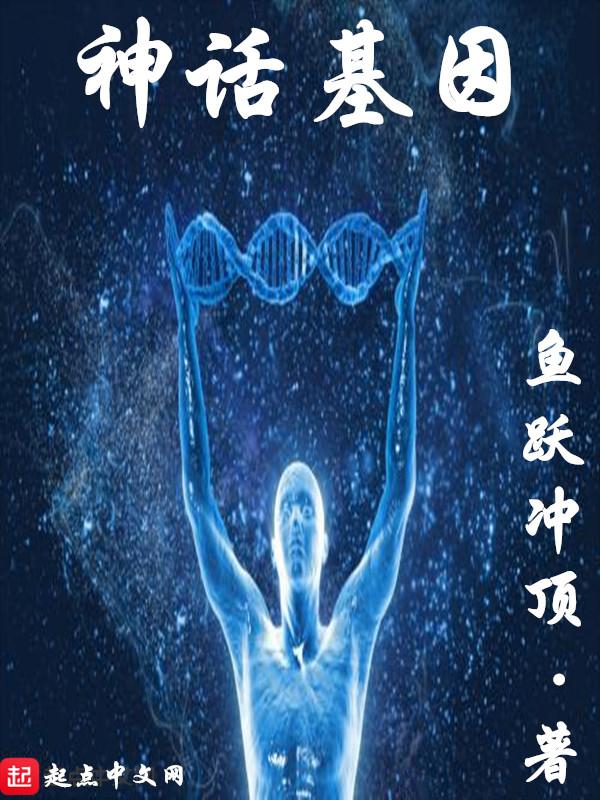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水浒传杀高俅是第几集 > 第164章 雷横入局(第1页)
第164章 雷横入局(第1页)
第二日清晨,何涛按照宋江的指点,怀揣公文匆匆来到郓城县衙。
晨光斜斜地洒在县衙大堂,知县大人端坐在案前,神情严肃。
何涛深吸一口气,恭敬地上前拜见,将生辰纲一事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知县眉头紧皱,沉思片刻后,当即命人传唤张文远。
不多时,张文远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大堂,脸上还带着几分慵懒。
张文远这几日正与阎婆惜如胶似漆,听闻要跟着何涛办事,顿时皱起眉头,支支吾吾地推脱:
“大人,小人近日事务繁杂,恐难抽身……”
知县脸色一沉,大手一挥,语气不容置疑:
“此事事关重大,休得多言!这几便听何涛差遣,不得有误!”
张文远无奈,只得耷拉着脑袋,极不情愿地应下,何涛心中暗喜,领着张文远便往军营而去。
待何涛和张文远离开后,宋江心中的计划开始加速运转。
宋江给小吏交代几句,出了县衙,脚步匆匆,首奔赌坊而去。
在嘈杂的赌坊中,一眼便瞧见了正在押注的雷横。宋江快步上前,一把拉住雷横的胳膊,压低声音道:
“兄弟,有要事相商!”说罢,也不管雷横愿不愿意,拉着他就往僻静的茶水铺子走去。
到了茶水铺子,宋江警惕地环顾西周,确定无人偷听后,从怀中掏出吴用写的密信,递到雷横面前。
雷横接过信,目光快速扫过,看到里面提到宋江、朱仝和自己三人名字,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微微颤抖:
“这个吴用什么意思?这可如何是好?那日我三人放过他们,那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动起手来,吃亏的是我们啊!”
宋江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紧紧握住雷横的手,目光中满是恳切,宋江知道,此刻正是拿捏雷横的绝佳时机。
停顿片刻后,宋江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先别管这个,那吴用不光送了这封感谢信,还附赠了十根金条!”
“什么?”雷横双眼猛地睁大,瞳孔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一把抓住宋江的手腕,急切地问道:
“金条在哪呢?”
宋江看着雷横那副财迷心窍的模样,心中暗自得意,庆幸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宋江早就了解了郓城县两位都头,朱仝为人忠义,家底殷实,又无不良嗜好,难以操控;而雷横好赌成性,久赌之下,爱财如命,此刻便是最好的突破口。
果然,听说有金条,雷横搓了搓手,脸上堆满笑意:
“哈哈哈,正是黄天不负有心人,我早就知道王进、晁盖这帮人是知恩图报的忠义之士,果然,幸亏当时放了他们!”
宋江脸色一变,急忙伸手按住雷横的肩膀,左右张望一番,压低声音提醒道:
“兄弟,小声些,小心隔墙有耳!”
随即,宋江脸上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神情,长叹一声:“兄弟,都怪哥哥不好,一时糊涂,被张文远和阎婆惜抓住了把柄,那十根金条,全都落入了阎婆惜那个贱人手里!”
“什么!”雷横“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怒目圆睁,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碗都跟着跳了起来,“那个臭娘们,老子早就看她不爽了,我这就去宰了那个臭表子!”说着,便要往外冲。
“兄弟!”宋江眼疾手快,一把拉住雷横,神色严肃,“切不可伤人性命,你我都是公门中人,做事须得谨慎!”
雷横不耐烦地一甩手:“嗨!那哥哥说,该怎么办?”
宋江沉思片刻,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起身说道:“兄弟,咱们这就去找那婆娘,到时候,一切看我脸色行事!”
二人快步来到阎婆惜住处。推开房门,只见阎婆惜正坐在梳妆台前,悠闲地摆弄着发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