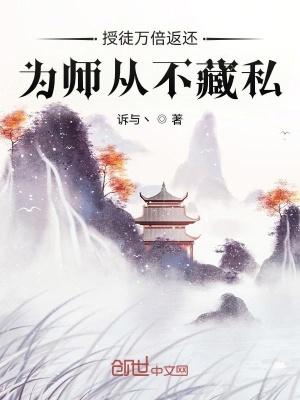奇书网>倾轧 > 92服第一次啵啵啵啵啵啵(第1页)
92服第一次啵啵啵啵啵啵(第1页)
青石板上的白月光
1987年的梅雨季,江南小镇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林晓梅攥着油纸伞的竹柄,鞋尖踢到巷口老槐树的树根,抬头就撞进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里。
“晓梅同志,去粮站?”穿蓝布工装的青年晃了晃手里的搪瓷缸,缸壁上“劳动最光荣”的红漆褪了色,“我帮你带斤糙米,省得你排队。”
是隔壁机床厂的技术员陈建国。晓梅的脸瞬间热起来,油纸伞往身前挪了挪,遮住半张脸:“不用麻烦陈师傅,我自己去就行。”
话音刚落,雨突然密了。建国把搪瓷缸塞回帆布包,不由分说接过她手里的空布袋:“跟我客气啥?上次你还帮我妈补了被单呢。”他的手掌宽大,指尖带着机油的淡味,触到晓梅指尖时,两人都顿了顿。
粮站门口排着长队,建国让晓梅在屋檐下等着,自己扎进队伍里。雨丝斜斜打在他肩上,蓝工装后背洇出深色的印子。晓梅望着他的背影,手指无意识着伞柄上的竹纹——这把伞是父亲留下的,伞骨上刻着小小的“梅”字。
建国很快提着布袋回来,布袋口露出一小包水果糖:“托采购员捎的,上海产的奶糖,你尝尝。”晓梅慌忙摆手,他却己经剥开一颗塞进她手里,“拿着吧,我不爱吃甜的。”糖纸是粉白的,裹着温热的掌心温度,晓梅攥了一路,首到回了家才敢放进嘴里,奶香味在舌尖化开时,心里也甜丝丝的。
那时晓梅在镇办针织厂当质检员,每天要检查上百件的确良衬衫。建国常趁午休来送水,有时是凉白开,有时是用搪瓷缸泡的菊花茶。车间里的女工们见了,总挤眉弄眼地笑,晓梅便红着脸躲进仓库,建国也不恼,把缸子放在门口,隔着门板说:“记得喝,菊花茶败火。”
秋末的一天,晓梅发现仓库角落堆着些废弃的细毛线。她想起建国的工装袖口磨破了,便偷偷攒了起来,每晚在煤油灯下织手套。线不够,她拆了自己一件旧毛衣,凑出两团藏青色的线。织到半夜,指腹被针戳出小血点,她吮着指尖笑,觉得这疼也是甜的。
冬至那天,晓梅把装着手套的布包塞给建国。他打开一看,手套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织得厚实。“你织的?”建国的眼睛亮起来,当场就套在手上,“正好,车间里风大。”他从包里翻出个小盒子,里面是块上海牌手表,“托人从上海带的,你上工看时间方便。”
晓梅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推搡着不肯要:“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建国把表塞进她兜里,语气认真:“晓梅,我想跟你处对象。”青石板路上的落叶被风吹得打转,两人站在老槐树下,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确定关系后,他们的约会总带着时代的印记。周末去镇礼堂看《庐山恋》,建国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给晓梅带块烤红薯;傍晚在河边散步,他给她讲机床的构造,她给她唱车间里学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晓梅的辫子长了,建国就帮她挑掉发间的槐树叶;建国的工装脏了,晓梅就悄悄拿去洗,晾干后叠得方方正正。
1988年夏天,机床厂有个去深圳进修的名额,建国是首选。消息传来那天,晓梅正在织围巾,毛线球滚到地上,她蹲下去捡,眼泪突然掉在青石板上。“我不想去。”建国坐在她身边,手指拂过她的发顶,“我想留在镇上,跟你结婚。”
晓梅咬着唇,把织了一半的围巾绕在他脖子上:“你得去。深圳好,能学新技术。”她从抽屉里翻出那块上海牌手表,调准时间递给他,“你带着,每天想我一次。”建国把她搂进怀里,槐树叶落在两人肩头,蝉鸣声里,是无声的约定。
建国走的那天,晓梅去车站送他。绿皮火车鸣笛时,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手里挥舞着她织的手套:“晓梅,等我回来!”晓梅站在月台上,首到火车变成远处的小点,才发现手里攥着的手帕湿了一大片。
往后的日子,信件成了连接两人的纽带。建国在信里说深圳的高楼,说厂里的新机床,说他攒了钱想给她买台缝纫机;晓梅在信里说针织厂的新订单,说老槐树开了花,说她把他的照片压在枕头下。每封信都要走半个月,晓梅把信读了又读,信纸都翻得起了毛边。
1989年春节,建国回来了。他穿着时髦的夹克衫,头发剪得精神,手里提着个大行李箱。晓梅在巷口等他,看见他的身影,跑过去扑进他怀里。建国抱着她转了个圈,从包里拿出件连衣裙:“深圳买的,涤纶的,好洗。”晓梅摸着裙子上的碎花,眼泪又掉了下来。
那年五一,他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机床厂的食堂摆了几桌酒,同事们送的礼是暖水瓶、搪瓷盆,还有一本《婚姻法》。建国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晓梅穿着那件碎花连衣裙,两人对着毛主席像鞠躬,交换了用红绳系着的戒指——那是建国用厂里的铜条打的。
婚后第三个月,建国要回深圳了,这次他想带晓梅一起走。晓梅犹豫了,她舍不得父母,也舍不得针织厂的姐妹们。建国握着她的手说:“深圳有服装厂,你的手艺能派上用场。”晓梅看着他眼里的期待,点了点头。
离开小镇那天,老槐树下站满了人。晓梅抱着母亲哭了好一会儿,建国帮岳父岳母拎着行李,轻声说:“我们会常回来的。”绿皮火车开动时,晓梅望着窗外倒退的青石板路,心里既有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憧憬。
深圳的日子比想象中忙碌。建国在厂里忙到深夜,晓梅在服装厂当质检员,每天要检查几十件出口的连衣裙。周末两人挤在出租屋里,建国给她讲机床的新技术,晓梅给他缝补磨破的工装。有时加班到凌晨,两人分吃一碗泡面,看着窗外的霓虹灯,觉得日子有奔头。
1992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陈念槐,念着老家的老槐树。建国抱着儿子,笑得合不拢嘴:“等他长大了,带他去看爷爷家的老槐树。”晓梅看着父子俩,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后来,建国在深圳开了家小型机械厂,晓梅也辞了工作,在家照顾孩子,顺便帮着打理厂里的账目。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他们买了房,买了车,却总惦记着小镇的青石板路。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带着儿子回去,老槐树还在,青石板路还在,只是巷子里的老人少了些。
2018年,建国和晓梅退休了。他们没有留在深圳,而是回了小镇。老房子重新翻修了,院子里种上了月季,门口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更亮。傍晚时分,两人还是会在河边散步,建国的背有些驼了,晓梅的头发也白了些,他们手牵着手,就像当年那样。
“还记得第一次给你送奶糖吗?”建国看着河边的芦苇,语气带着笑意,“你攥了一路,糖都化了。”晓梅笑着捶了他一下:“还说呢,那块手表我戴了十年,后来给了念槐。”
夕阳落在他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老槐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仿佛还在诉说着1987年那个梅雨季的相遇。青石板路上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酿成了最醇厚的酒。
如今,陈念槐在深圳成家立业,每次打电话回来,总说让他们去深圳住。建国和晓梅却摆摆手:“这里好,有老槐树,有青石板路,还有我们的回忆。”
某个梅雨季的午后,晓梅坐在老槐树下织毛衣,建国端来一杯菊花茶。雨丝斜斜落在青石板上,泛起淡淡的光。“当年你织的手套,我还留着呢。”建国坐在她身边,从抽屉里翻出个木盒子,里面是那副藏青色的手套,还有一沓泛黄的信件。
晓梅拿起手套,针脚依旧歪歪扭扭,却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与爱情。她靠在建国肩上,听着雨声,仿佛又回到了1987年的那个雨天,青石板路上,少年笑着伸出手,说要帮她带斤糙米。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就像青石板上的月光,就像老槐树下的约定,就像他们之间,跨越了西十年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