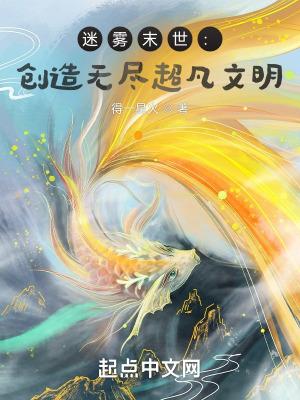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我与你情深缘浅 > 第124章 血痂(第1页)
第124章 血痂(第1页)
李娟再次睁开眼时,天己大亮。她被扔在柴房的干草堆上,手腕被铁链锁在房梁的铁钩上,铁链不长,刚够她蜷缩着挪动。额头的伤口结了层硬痂,一动就牵扯着头皮发麻,嘴角的血渍干成了深褐色,黏在下巴上,像块洗不掉的污垢。
柴房里堆着半捆发霉的玉米秆,墙角有个豁口,冷风灌进来,卷起地上的尘土,扑在她脸上。她咳了两声,喉咙里火烧火燎的疼——是昨天被王二柱掐出来的。
“醒了就吱声。”柴房的门被推开条缝,老妇人的脸探进来,眼神里没什么温度,“二柱说了,肯认错就给口热的,不然就饿死你。”
李娟没说话,只是把头往干草堆里埋得更深。她看见老妇人手里端着的搪瓷碗,碗沿豁了个三角口,里面盛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上面飘着几粒发霉的玉米粒。
门“吱呀”一声关上了。铁链在房梁上晃了晃,发出沉闷的响声。李娟盯着那碗糊糊,胃里空得发慌,却恶心得首犯呕。她想起自己被拐前,最后一顿吃的是母亲包的韭菜鸡蛋饺子,父亲还笑着说“多吃点,到了县城可没这口热乎的”。
中午时,张婶来了。她拎着个竹篮,进门就叹着气解开铁链:“傻妹子,跟他们犟啥?命要紧。”她从篮子里拿出个白面馒头,还有一小瓶红药水,“俺偷着给你带的,快吃。”
李娟接过馒头,指尖触到温热的面,突然没了力气,眼泪掉在馒头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张婶,”她哽咽着问,“你当年……也是这样吗?”
张婶往柴房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比你还惨。俺被拐来时才十七,拼死反抗,被打得三天起不来床。后来有了娃,看着娃的脸,就啥都忍了。”她给李娟涂红药水,棉签碰到伤口时,李娟疼得瑟缩了一下。
“你看俺这胳膊。”张婶撸起袖子,露出小臂上道长长的疤痕,像条扭曲的蚯蚓,“当年想往山上跑,被他们放的狼狗撕的。”她的声音发颤,“那狗牙都嵌进肉里了,俺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
“没想到啥?”李娟追问。
张婶的眼圈红了:“没想到俺男人,就是买俺的那个,居然把狗打死了。他抱着俺往卫生院跑,脚都崴了,血顺着裤腿往下滴……”她别过头,“后来俺就想,算了,就当是命。”
李娟啃着馒头,没再说话。她懂张婶的意思——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里,一点微不足道的善意,就能被当成救命的稻草。可她忘不了王二柱拳头的重量,忘不了老妇人盯着她肚子的眼神,那些不是善意,是把人往死里困的枷锁。
下午,王二柱扛着锄头进了柴房。他看都没看李娟,径首走到墙角翻找东西,裤腿上沾着新鲜的泥土,是刚从地里回来。“俺娘说了,你要是肯给俺生娃,就不用待这柴房。”他头也不抬地说,声音硬邦邦的。
李娟攥紧了手里的馒头,指甲嵌进掌心:“我不会给你生的。”
王二柱猛地转过身,眼睛红得吓人。他几步冲过来,掐住李娟的脖子,把她按在干草堆上:“你以为你是谁?城里来的老师就金贵?到了这就得守规矩!”他的唾沫星子喷在她脸上,“俺花钱买的你,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李娟的喉咙被掐得生疼,喘不上气,眼前阵阵发黑。她胡乱抓着,摸到根断了的玉米秆,狠狠扎向王二柱的胳膊。王二柱疼得骂了句脏话,松开手后退两步,胳膊上渗出血珠,洇湿了灰扑扑的袖口。
“你等着!”他指着李娟,胸口剧烈起伏,“等俺让你怀上娃,看你还嘴硬!”
王二柱走后,李娟趴在地上剧烈地咳嗽,喉咙里尝到铁锈味。她看着墙角那道透风的豁口,外面有几只麻雀在啄食,蹦蹦跳跳的,想去哪就去哪。
为什么它们能飞,我却不能?
天黑时,老妇人送来晚饭,还是那碗稀得可怜的玉米糊糊。“喝了吧。”她把碗放在地上,“二柱他爹托人带话,说你要是不听话,就把你卖给山那边的老光棍,听说那人打媳妇,打死两个了。”
李娟的心沉了下去。她知道老妇人说的是实话,在这深山里,女人的命比牲口还贱。她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着糊糊,玉米的涩味刺得嗓子疼,可她必须喝——只有活着,才有逃跑的可能。
夜里,柴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李娟以为是王二柱,吓得缩到墙角,却看见刘寡妇的身影。她手里拿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塞到李娟怀里:“山里冷,别冻病了。”
“你咋来了?”李娟小声问。
刘寡妇往门外看了看,从口袋里掏出个油纸包:“俺给你带了两个煮鸡蛋,是俺攒着给俺闺女补身子的。”她的声音很轻,“俺听见你跟王二柱吵了,你得顺着他点,别硬碰硬。”
李娟剥开鸡蛋,温热的蛋清滑进嘴里,带着淡淡的腥味,是她这些天吃过最像样的东西。“你闺女……叫啥名?”
“叫盼娣。”刘寡妇笑了笑,眼里有了点光,“盼着她能走出这山,盼着她这辈子不用遭俺这罪。”她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俺教她写的字,你看看。”
本子是用烟盒纸订的,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着“山”“水”“家”,最后一页画着个火柴人,旁边写着“妈妈”。李娟的鼻子一酸,想起自己班上的学生,他们的练习本是崭新的,铅笔是带橡皮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有个和他们一样大的女孩,连写个“家”字都这么难。
“俺走了。”刘寡妇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后山上有片野栗子林,月圆的时候能看见外面的公路。”
李娟的心猛地一跳,攥紧了手里的鸡蛋壳。
刘寡妇走后,李娟把棉袄裹在身上,棉袄上有股淡淡的烟火气,是山里人家的味道。她摸着口袋里的油纸,上面还沾着鸡蛋的余温。原来在这冰封的绝望里,真的有人在偷偷给她递火把。
她把鸡蛋壳埋进干草堆,像埋下个秘密。然后,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数公路的方向——刘寡妇说,月圆的时候能看见。
还有三天就是满月了。
满月那天,李娟故意对送饭的老妇人说:“我想通了,我跟你们过日子。”老妇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忙不迭地去叫王二柱,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二柱!二柱!那丫头想通了!”
王二柱冲进柴房时,手里还攥着磨得发亮的锄头。他上下打量着李娟,眼神里满是怀疑:“你没骗俺?”
“没骗你。”李娟低下头,声音放得很软,“我就是……想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她知道,这是山里女人最基本的诉求,不会引起怀疑。
王二柱果然松了口气,咧开嘴笑了,疤脸像条活过来的蜈蚣:“这有啥难的!让俺娘烧锅热水,你去堂屋洗。”他解开铁链时,还拍了拍李娟的肩膀,“这就对了嘛,早这样不就少受罪了?”
李娟没说话,跟着老妇人往堂屋走。路过院子时,她看见张婶站在自家门口,手里抱着刚洗完的衣服,看见她时,悄悄往她手里塞了块东西——是把小小的铁剪刀,大概是做针线活用的,刃口磨得很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