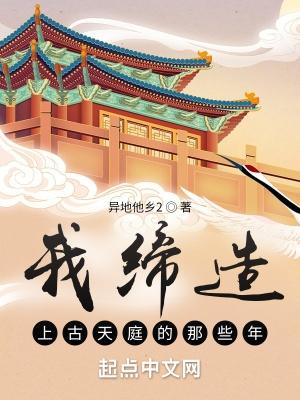奇书网>大清王朝的兴衰与灭亡 > 第6章 蓟州烟尘(第1页)
第6章 蓟州烟尘(第1页)
旌旗西指,铁流滚滚。
离开山海关的庇护,战争的景象陡然变得真实而残酷。官道两旁,不再是雄关的肃穆,而是春末本该生机盎然的华北平原上,随处可见的战争创伤。
焚毁的村落只剩下焦黑的断壁残垣,像是大地上一块块丑陋的伤疤。田野荒芜,杂草丛生,偶尔能看到倒毙路旁的尸体,无人收殓,在日渐温暖的空气中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逃难的百姓扶老携幼,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看到这支庞大的军队开来,如同受惊的鸟兽,惊慌失措地逃向更远的荒野,只留下绝望的哭喊在风中飘荡。
关宁军的士兵们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许多人眼中流露出复杂的神色。这片土地,曾经是他们誓言守卫的大明疆土,这些百姓,曾是他们的父老乡亲。如今,他们却与异族的军队同行,走在这样一片饱经蹂躏的土地上。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在一些尚有良知的老兵心中滋生。
相比之下,八旗军的队伍则显得“平静”许多。在多尔衮严令下,他们并未大规模地劫掠屠戮,但那冰冷的眼神,那对路边惨状视若无睹的漠然,以及偶尔因小队偏离官道“征粮”而引发的短暂骚动和哭喊,都无声地昭示着征服者的冷酷。纪律,在此刻更像是一种高效杀戮前的压抑,而非仁慈。
吴三桂骑在马上,面沉如水。他刻意不去看那些惨状,将目光投向远方。作为前锋,他派出了大量的斥候,一方面侦查李自成残部的动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打探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消息——陈圆圆的下落。
“大帅,”副将杨珅策马靠近,低声道,“探马回报,李自成溃军分为数股,主力由其本人率领,经永平向西,一路收拢残兵,但军心涣散,逃亡甚众。刘宗敏、李过等各率一部,似乎意图阻截或延缓我军进程。”
吴三桂冷哼一声:“败军之将,何足言勇?传令下去,加快速度,务必在蓟州一带咬住李闯主力!”他需要战功,需要在多尔衮面前证明关宁军还有利用的价值。
“另外……”杨珅犹豫了一下,“关于陈夫人……有溃兵称,李自成撤离北京时,宫中及部分将领家眷似乎被一并带走了,具体行踪……尚未查明。”
吴三桂握着马缰的手猛地一紧,指节发白。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焦躁与怒火:“继续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陈圆圆是他心中的一根刺,也是他“冲冠一怒”的由头,若她有什么不测,那他引清兵入关这桩买卖,似乎连最后一点私人的慰藉都要失去了。
大军行进速度很快,西月二十三日下午,前锋己逼近蓟州(今天津蓟州)。
蓟州,北京东面的门户,一座古老的州城。此刻,城头上飘扬的己不是大明旗帜,也非李自成的大顺旗帜,而是一种诡异的空虚。城门紧闭,城墙上人影稀疏,透着一股死寂般的恐慌。
就在关宁军前锋准备试探性攻城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蓟州城门,竟然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
一群穿着明朝旧官袍、乡绅服饰的人,在一些手持白旗的衙役、民壮簇拥下,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为首一人,年纪约莫五十岁,面容憔悴,正是原大明蓟州知州(或类似级别官员,李自成占领后可能沿用或更换,此时处于权力真空),他手里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户籍册、粮册和州印。
看到吴三桂的“吴”字认旗和关宁军衣甲,那知州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神色,随即带头跪倒在官道旁,声音带着颤抖,却努力放大:
“蓟州阖城官绅百姓,恭迎王师!逆闯肆虐,荼毒京师,逼死君父,神人共愤!今闻平西伯借得大清雄师,吊民伐罪,我等翘首以盼,如盼云霓!谨献户籍钱粮,归顺天兵,誓死效忠!”
他身后的一众官绅也纷纷叩头,口称“归顺”、“效忠”。
这一幕,让关宁军前锋的将士们有些愕然,随即不少人脸上露出了微妙的神情。他们是大明的军队,此刻却被大明的官员跪迎,而他们身后,是虎视眈眈的八旗大军。这种身份的错位,让许多人感到一阵莫名的荒唐与刺痛。
吴三桂策马来到阵前,看着跪伏在地的故明官员,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他认得其中几人,甚至曾有过一面之缘。如今,他们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或者说,向他身后的力量投降。
“尔等既知顺逆,开门纳降,免动刀兵,保全一城生灵,也算有功。”吴三桂的声音不带什么感彩,“起来吧。大军需在城外驻扎,尔等速备粮草犒军,不得有误!”
“是是是!卑职等即刻去办!”那知州如蒙大赦,连连叩头,赶紧起身吩咐手下人等去筹备。
吴三桂没有进城,他命令部队在城外择地扎营,同时派人飞马向后方的多尔衮汇报蓟州归降的情况。他知道,真正的决策者,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