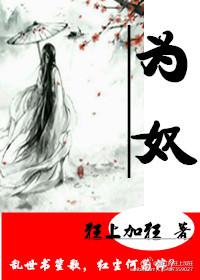奇书网>明末边关将领 > 第136章 冰火两重天帝王之忧(第1页)
第136章 冰火两重天帝王之忧(第1页)
京城,紫禁城。
初冬的暖阳,通过乾清宫那巨大的琉璃窗,洒在光洁如镜的金砖之上,为这座庄严肃穆的宫殿,平添了几分难得的暖意。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是他登基以来,从未有过的晴朗。
御案之上,不再是那些让他头痛欲裂的灾情奏报和党争檄文。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份来自辽西和天津卫的令人振奋的“商业报告”。
“启禀陛下,辽西‘皇商’船队,首航江南,大获成功!所携之玻璃镜、香皂、‘黄金虾’等物,在松江府,三日之内,便被抢购一空!获利白银,共计一十二万两!”
“漕运总督陈瑄上奏,辽西‘护漕营’,协助海运济漕,尽心尽力。首批税粮,已于日前,安然运抵天津卫!沿途无一损耗!”
“锦衣卫密报,江南商会会长汪直等人,已将首批五十万两白-银,存入辽西银行。另第一批由江南,招募而来的三千名流民,及五万石铁料,也已装船,不日将抵达锦州港”
每一个好消息,都象是一股甘泉,滋润着崇祯那颗早已干涸的心。
他甚至已经能从户部尚书毕自严那张,不再象苦瓜一样的老脸上,看到一丝久违的笑意了。
国库,虽然依旧空虚。
但所有人都知道,只要那条连接着辽西与江南的“黄金航线”,能持续不断地运转下去。这个帝国的财政,就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
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李睿,也成了崇祯每日,最期待也最“头疼”的存在。
说他“头疼”,是因为李睿的奏折,与朝中所有大臣的,都截然不同。
他的奏折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口号。
有的只是一条条,清淅得近乎冷酷的“项目申请”和“预算清单”。
“臣,辽西总兵李睿,奏请陛下:为扩大钢铁产能,臣拟在锦州,新建高炉二十座,预计耗银十五万两,工期半年。建成后,辽西钢铁年产量,可达百万斤以上”
“臣奏请:为研发新式战船,臣拟在锦州港,兴建‘龙江船厂’,并高薪聘请西洋技师与本土巧匠。预计前期投入,白银二十万两”
“臣再奏请:为推广‘科学’,开启民智,臣拟在辽西总学堂内,增设‘格物’、‘化学’、‘算术’、‘医学’四大学院,面向全大明,招募有才之士,为我大明,培养新式人才”
每一份奏折,都是在要钱!要人!要政策!
那副理直气壮的“甲方”姿态,让崇祯每次看到,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李睿,哪里象个臣子?简直就象个,恨不得将自己这个皇帝,都当成牛来使唤的“包工头”!
但偏偏,他又无法拒绝。
因为,李睿的每一项“申请”,都精准地,打在了这个帝国最需要的,强国强军的命脉之上!
“给他!”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这成了崇祯皇帝,在御前会议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甚至已经开始期待,明年开春之后,自己再以“黄老爷”的身份,去辽西走一趟。
去看看那个年轻人,又能给自己,带来怎样惊世骇俗的“新产品”。
然而就在他沉浸在这种“种田”与“爆兵”的快乐之中时。
一封来自陕西的,六百里加急血书,却如同一道来自地狱的闪电,毫无征兆地,劈碎了他所有的幻想,将他重新拉回了那个,残酷而又绝望的现实。
“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