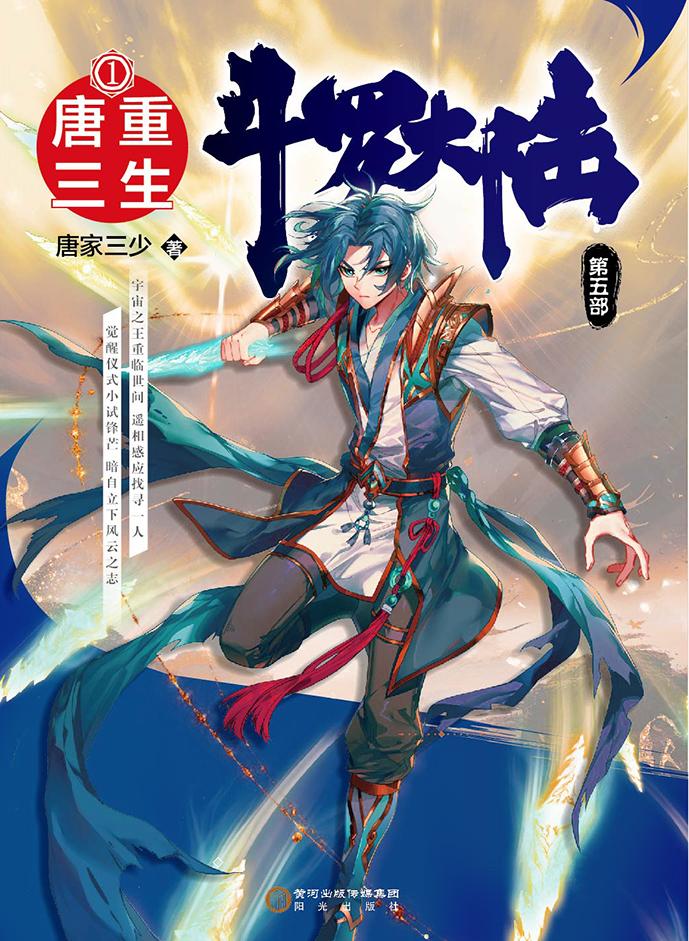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我真的想兄弟 > 他最羡慕的男人(第2页)
他最羡慕的男人(第2页)
春江月将靴子拿到跟前,觍着脸说道:“阿姊,帮我把这靴子洗了罢,很久没洗了,穿着难受。”
花江月:“……”
春江月见她接过靴子,心里想着,洗一双也是洗,洗两双也是洗……
于是他对众人说道:“将你们的靴子脱下来罢,我阿姊顺手替你们洗了。”
兵舍里的七八位少年一愣,慌忙摆手道不用。
许是念着时常偷穿长风烈干净衣裳的恩情,春江月看向长风烈道:“阿烈,你快脱下来罢,我阿姊替咱们一块儿洗了,瞧你那鞋湿的……”
见花江月也朝自己看来,长风烈登时神经紧绷,那双汗湿的布鞋里,脚趾头都抠紧了。
“不……不……不用了……”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咱们都已经是结拜兄弟了,我的阿姊就是你的阿姊……”春江月说着就朝长风烈走来。
长风烈慌忙去拂他的手,春江月却不依不挠,两个青葱少年很快在铺上滚作一团。
“不……不用了,真的不用……别……别……”
春江月闹得挺欢,脱下长风烈一双鞋后见他倒在铺上一脸羞愤样,只以为他是在跟自己客气呢。
见少年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花江月只得宽慰道:“阿春说的是,你们都是禹州来的,又跟阿春是朋友,以后还要一起在这里待上许久,把我当作自家阿姊便是了,不必客气。”
“就是就是。”春江月说着又要去脱九方月的靴子。
整个兵舍里春江月和他二人走得最近,春江月与九方月同岁,两人也闹得更开,而长风烈要小他二人一岁,是他们兵舍里年纪最小的。
不同于长风烈时时让着春江月,九方月才不惯他,两人在铺上哄闹了好一番才停下来。
九方月理了理衣裳,有些不好意思地冲花江月道:“那……有劳江月姊姊了。”
闻言,春江月给他背上来了一掌,豪迈地说道:“嗐!还什么江月姊姊,太见外了,都是自家兄弟,跟着我叫阿姊得了。”
“……阿……阿姊……”
“……阿姊……”
花江月点头应下。
春江月从床铺下掏出个旧包袱,将三人的鞋靴塞到包袱里后跑到花江月跟前得意洋洋道:“阿姊,他们的脚比我的还臭。”
九方月:“……”
长风烈闻言,简直杀人的心都有了,把脑袋蒙在被子里半天不出来。
人都走了许久了,长风烈还气鼓鼓地蒙在被子里。
九方月觉得好笑,走过去将他拖了出来:“你快出来罢,江月姊姊带的东西都快被那些小子吃完了,你别等会不得尝……”
长风烈呆呆地走到桌前,肉干已经没了,栗子糕还剩半块。
也不知是哪个嘴欠的,咬了一半扔在那儿。
长风烈拿起那半块栗子糕,走到门口站着,正盯着大门的方向发呆,却听见路过的两个士兵议论道:
“方才春江月的阿姊又来了。”
“唉——你还在想?人都已经名花有主了。”
“什么名花?我看是半老徐娘还差不多……”
长风烈蹙眉,想起了花江月来时的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