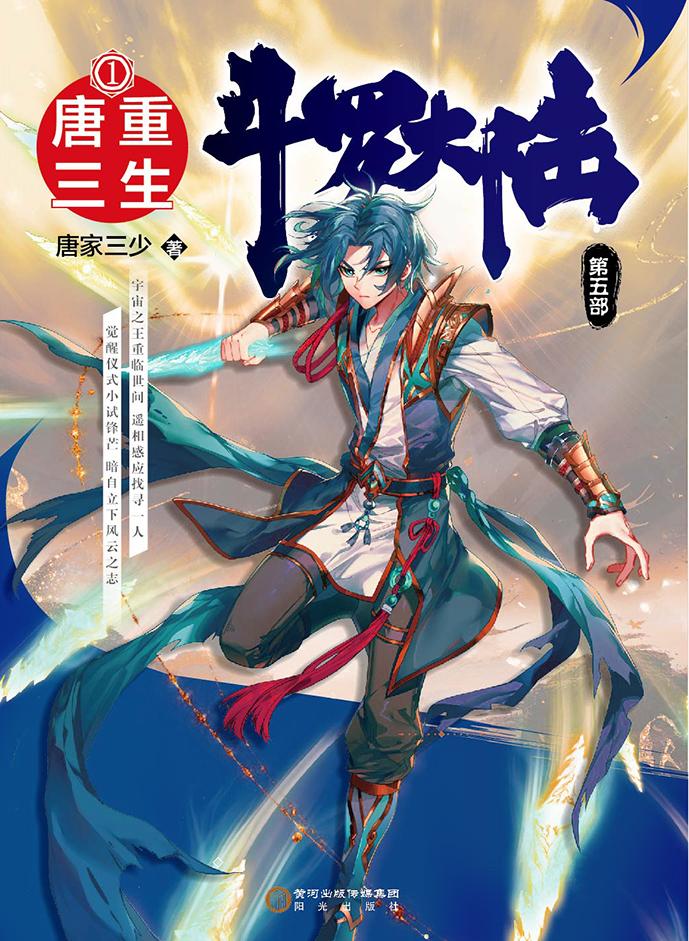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从盛夏到深秋的文案 > 历史该被看见(第4页)
历史该被看见(第4页)
一位坐在前排的华裔女学者悄悄递给他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低声道:“Goodjob。Takeadeepbreath。”
他接过水,低声道谢,喉咙干涩得发疼。
后续的报告内容,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脑海中反复回放着刚才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画面,应该没有一句话不得体,应该没有丢人。
他从未在公开场合如此情绪失控,如此“不专业”。
可是,奇怪的是,他心中并没有丝毫后悔或懊恼,反而有一种卸下了千斤重担般的释然,以及一种为那些沉默的亡灵发出了声音的、悲怆的慰藉。
会议茶歇时,沈知时独自一人站在靠窗的角落,望着窗外柏林灰蒙蒙的天空。
手中的矿泉水瓶壁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冰凉的温度透过掌心,让他沸腾的血液稍稍冷却。
几位来自欧美不同国家的学者主动走过来与他交谈,表达了对他们才报告内容的兴趣,也对他刚才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
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这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他注意到,那个日本学者很快便离开了会场,没有出现在茶歇区。
这时,之前递给他水的华裔女学者微笑着再次走近。“Dr。Shen,ImSusanWang,watETHZurich。”她递过一张名片,动作优雅,“Yourresearchisveryiing,especiallythemodelstrupartforecologicalimpactassessment。Ihopeweexgeideasiftheresace。”(沈博士,我是苏珊·王,在ETHZurich工作。你的研究很有意思,特别是关于生态效应评估的模型构建部分。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交流一下。)
“Thankyou,ProfessorWang。”沈知时双手接过名片,恭敬地说。苏珊·王看起来四十多岁,气质干练,目光温和而睿智。
“obesoformal。JustcallmeSusan。”她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丝感慨,“Formanyyears,Iverarelyseenayoungpersonwithsuchedgeandbaeataniionalference。Somethingsbesaiddiplomatically,butonmattersofprinciple,onemustbeclear。Youdidtherightthing。”(不必客气。叫我苏珊就好。很多年了,很少在国际会议上看到像你这样有锋芒、有骨气的年轻人。有些事,可以委婉,但原则问题,必须清晰。你做得对。)
沈知时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Iwasjust……saidwhatIthoughtIhadtosay。”(我只是……说了我认为必须说的话。)
“Iknow。”苏珊·王理解地点点头,眼神中带着阅历赋予的通透,“Sometimes,silenceismisinterpretedasacquiesce。Bytheway,”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YourreportmentionedNanjingsurbanmemory,whichremindedmeofsomething。AfriendofmiNanjingUystudiesurbanhistoryandpublicmemory。Ifyoureiedinuandingyourresearchareafrommoredimensions,perhapsIcouldintroduceyou。Geographicaldataistheskeleton,butthoseoralhistories,socialmemories,mightbethefleshandblood。”(我知道。有时候,沉默会被误解为默许。对了,你报告里提到南京的城市记忆,让我想起一件事。我在南京大学有一位朋友,是研究城市史和公众记忆的。如果你有兴趣从更多维度理解你的研究区域,或许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地理数据是骨骼,而那些口述历史、社会记忆,可能是血肉。)
这个提议让沈知时心中一动。他之前从未想过将冷冰冰的遥感数据与活生生的城市记忆联系起来。这似乎为他封闭的研究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甚至……
或许也为他理解林叙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南京,提供了一条隐秘的路径。“Thatwouldbewonderful,thankyouverymuch!”(那太好了,非常感谢您!)他真诚地说,感到一种久违的、对知识探索本身的期待。
与苏珊·王道别后,沈知时的心情复杂难言。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参加晚上的招待酒会,而是选择回到了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
柏林的夜晚灯火阑珊,远远传来城市的喧嚣,却更衬得房间内的寂静。他脱下西装外套,松开衬衫领口,疲惫地倒在床上。
白天发生的一切如同电影镜头般在脑海中回放。
那个日本学者挑衅的眼神,自己不受控制的激烈反应,台下那些震惊、支持、或许也有不解的目光,还有最后那阵如同潮水般的掌声……
这一切,都与他规划中平静的学术道路截然不同。
他拿起手机,下意识地点开了那个已经许久没有新消息的聊天窗口。头像是一片虚无的灰色。
最后一条信息,还停留在他出国前的那个除夕,他发出的那句:“新年快乐。”对方没有回复。
他鬼使神差地,在输入框里打下了一行字:“今天,在柏林,为了南京,和人争执了。”
指尖悬在发送键上,久久未能落下。
他有什么立场对林叙说这些呢?他们之间,早已隔着一片比慕尼黑到南京更遥远的、无法跨越的荒漠。
最终,他还是逐字删除了。那短短一行字,像投入深潭的石子,连涟漪都未曾激起,就沉入了黑暗。
他关掉手机屏幕,房间陷入彻底的黑暗。窗外的城市之光微弱地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光影。他闭上眼,仿佛又看到了高三那个午后,林叙转过头来,对他露出一个清淡的、带着些许疲惫的笑容。
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未来似乎有无限可能,沉重的历史还只是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段落。
而如今,历史以这样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与他个人的情感、与他冷冰冰的学术研究猛烈地撞击在一起。
他意识到,有些东西,是无法仅仅用理性和数据来完全覆盖和解释的。
比如一个民族的集体伤痛,比如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比如那个叫林叙的人,在他生命中留下的、至今仍在隐隐作痛的烙印。
柏林之夜深沉。沈知时在异国他乡的床上,辗转反侧。他知道,有些东西,从今天起,已经不一样了。
无论是他对学术的理解,还是他对那段尘封过往的态度。
而关于林叙的谜题,似乎也在这场关于历史真相的激烈争辩后,透出了一丝微弱、却无法忽视的曙光。
他隐约觉得,解开个人心结的钥匙,或许并不仅仅在于追问过去,更在于如何面对现在,如何构建未来。
那个未来里,或许依然没有林叙,但应该有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