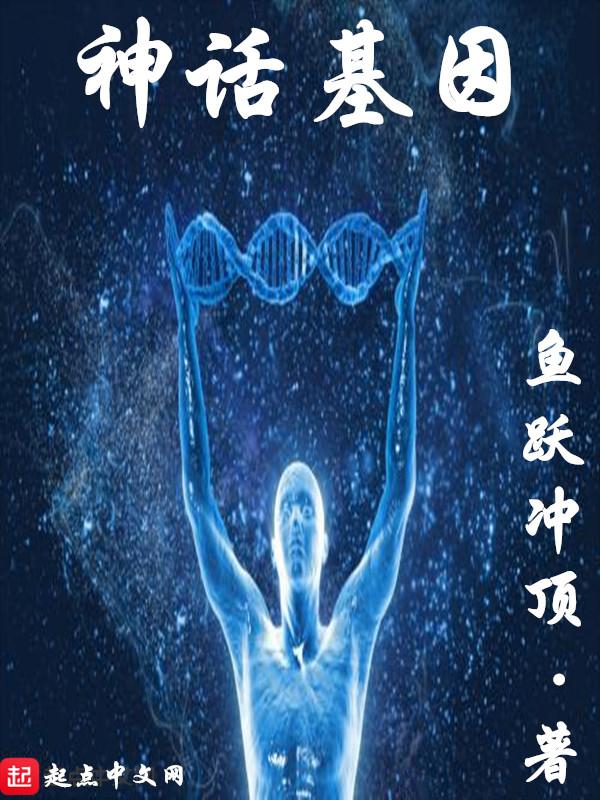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沉重的翅膀作者 > 第六章(第3页)
第六章(第3页)
汽车的小窗里,方文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一闪而过。
贺家彬对万群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你那里去!”他发现,
万群的眼睛里,好像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
她怎么了这神经质的女人!
四
这栋楼房,准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盖的,四层楼,像新建的五层楼那么高。对一
个年轻而健康的人来说,爬四层楼梯,算不了什么。叶知秋虽然还算健康,但是,
头发的脱落、皱纹的加深、牙齿的松动、心脏机能的衰退,都足以说明四十多个年
头里,有多少事情曾经发生、过去。雨水就是这样一滴滴地穿透石头,花岗岩就是
这样地风化,生命就是这样地更替,这一个瞬间便这样被下一个瞬间所淘汰。她也
会被淘汰,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就像头发不知何时开始脱落,皱纹不知何时在眼
角、额头聚集,牙齿何时变长,心脏从哪一个节拍上开始出了故障。然而,已经稀
疏的头发还在装饰着头颅,皱纹也不再会使她那不美的面孔更丑,牙齿也还在嚼着
维系生命的食物,心脏也还在拼却全力地把血液挤压到躯体的各部分……生命的天
职,蕴含着怎样不屈不挠而又自我牺牲的精神!爬到二楼,呼哧呼哧,胸口像个破
风箱在呱嗒、呱嗒地响着。
叶知秋靠在栏杆扶手上休息一下,揣测着这样冒昧地拜访一个大人物,会遭到
一个什么样的对待楼道里传来的一切音响全是不顾一切的、理直气壮的,仿佛都
在宣告着自己存在的合理:剁饺子馅的声音,婴儿啼哭的声音,弹钢琴的声音……
热闹的星期天。那是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弹琴的人总也不能流畅而连贯地弹下去,
让叶知秋心里起急。仿佛要帮弹琴的人加把劲儿,她按着记忆里的旋律,手指在栏
杆的扶手上习惯地掠过,好像那是一排琴键。她喜欢这个曲子,念中学的时候,她
常常在那架弃在礼堂角落深处的钢琴上弹它。那架钢琴又老又破,下过十八层地狱
似的,遍体鳞伤,磕磕疤疤。好几个音已经不准,调都没法调了。好像一个漂泊了
一生,到了风烛残年,又聋又瞎的孤老头子。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枝,透过宽敞
的玻璃窗,洒在礼堂的地板上。那和声里充满着幻想的力量。念大学以后,她就很
少弹琴了。那是没有工夫幻想的年月,而且,幻想是什么是虚无缥缈、是游手好
闲、是有闲阶级的情调……工作以后,她克勤克俭,还是买了一架琴。“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琴在一张旧毯子底下睡了十年。现在倒是可以弹了,但她早已没有那
个心情:幻想、和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这熟悉的,因为不熟练而显得遥远了的、模糊了的旋律,使她想要流泪——使
她的心稍稍有点发紧的眼泪。
像有意和这琴声作对,有谁在狠狠地、挑战似的用锤子敲击着什么:乒!乒!
乓!乓!叶知秋有点奇怪,一位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居然能和凡人一样,住在这公
寓式的房子里别是贺家彬记错了地址不会,他说过他曾经来这里坐过、聊过。
当然,也不能算什么凡人,这里至少是司、局级干部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