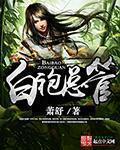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txt在线阅读 > 第176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第2页)
第176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第2页)
两部人马喊杀声震天响,脚下推进动作却很慢。所有将士都绷紧了神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同惊弓之鸟,只待城头稍有异动,两部人马便立刻靠拢,坚决不再给守军分割冲垮本部的机会。
南城门上,朱亮祖身披铁甲,手扶雉堞,面色阴沉地注视着城下的动静。其人身边一名心腹部下指着南城下紧张兮兮的陈通部,嗤笑道:
“千户,您看这些人的服饰,不就是前几天在北城门下被俺们冲垮的那支贼兵吗?瞧他们那怂样,哪有半点攻城的样子!哈哈哈!”
不消部下提醒,朱亮祖早已发现在阵后紧张指挥队伍的陈通。
他握住腰间刀柄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一股强烈的冲动在胸中翻涌,打开城门,带人冲出去!再冲垮他们一次,砍掉贼将的首级,用贼人的血洗刷前日突围的狼狈!
但最终,他还是缓缓松开了刀柄,嘴角扯出一个不屑的冷笑,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
“哼!贼将这么快就学乖了,想诱老爷出城?真当老爷是瞎子,看不到西面坡后多出来的那股骑兵么?”
本就只有三千余人的战场上,一下增加七百多人的骑兵,确实瞒不住城墙上视野开阔的守军。
不过,朱亮祖放弃出城反击的真正原因,却不是发现了红旗营新增的骑兵。
三日前那仗,看似小胜,实则惨烈的反击,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朱亮祖的心火。
朱亮祖选择出兵的时机极好,出其不意冲垮了陈通部庐江军,还差点裹挟溃兵冲垮第二阵费聚部,却被随后反应迅疾的常遇春部主力死死围住。
虽然凭借个人悍勇和暗器偷袭侥幸突围,但朱亮祖耗费无数心血拉起的数百精锐兵马,却在突围血战中折损了大半。更令他心痛的是,大半宗族子弟也陷在重围之中,生死未卜。
战后清点,六安城中守军仍有近一千六百人,但朱亮祖赖以在乱世中立足的“朱家军”已残,其人麾下那些或被他吞并,或主动依附的小军头,再看向他的眼神,便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若不是大敌当前,加上他朱亮祖凶名在外,积威尚在,恐怕早有人跳出来质疑他这个“义兵千户”的位置能不能挪一挪了。
经此一战,朱亮祖对红旗营的战力也有了清醒认识——绝不仅是某个或某几个将领的勇猛,而是整支军队都拥有恐怖的组织力和韧性。
换成其他反贼或地主团练武装,三千余人的军队,被连续攻破两阵冲散千余人,基本就要大溃了。
可红旗营呢?非但没溃,反而能在极短时间内组织起凶猛的反扑,将势头正盛的“朱家军”团团围住。这种组织力,太恐怖了!
莫说朱亮祖现在精锐已残,便是“朱家军”俱在,他也不敢再贸然出城,去硬撼这支大军了。
守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出城,必是死路一条!
东城墙下,攻城战斗已经打了近一个时辰,常遇春仍未披甲,驻马于阵前,脸色越来越凝重。
虽说一开始就定下了诱敌出城的策略,但为了避免被朱亮祖识破,常遇春严令负责主攻东城的刘聚和佯攻北城墙的费聚两部必须真打。
刘聚山贼出身,麾下还有几十个老弟兄,却被常遇春收拾得服服帖帖,明知任务凶险,也不敢有丝毫违抗,只能硬着头皮,驱使部下顶着城头滚木擂石和如雨的箭矢,一波波地发起猛攻。
而费聚所部的任务本是策应主攻,压力相对小些,但他却打得更猛。
红旗营攻打五河时,他就投效了石山,破城后便出任指挥使,其部后来虽然升为甲等营,却屈居比他晚很久投军的常遇春之下。
费聚有自知之明,对骁勇善战的常遇春倒也心服,但作为元帅元从,终究要些脸面。
三日前那一战,若非常遇春当机立断率亲兵截击,费聚所部很可能也会被朱亮祖和庐江溃兵冲垮,后果不堪设想。
怀着这份憋屈,费聚今日便冲杀在第一线,硬是将佯攻打成了主攻,士卒们见指挥使如此拼命,也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一度有十余人登上了东城墙,差点破城。
可惜,最终还是在朱亮祖悍不畏死的反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下,费聚本人也在混战中被流矢所伤,左臂中箭,险些被留在了城墙上。
仗打到这份上,常遇春算是看出来了,朱亮祖怕是不可能再出城了。
而红旗营这边,一般人即便攻上了城墙,也很容易被朱亮祖这厮赶下来,不想白白折损麾下将士性命,就只能撤兵。
“鸣金!收兵!”
冯国胜所部骑兵在外围警戒,掩护攻城部队如潮水般撤回本阵。这次才策马奔来,一脸的疑惑和不甘。
“常大哥,姓朱的当真是属王八的?铁了心缩在壳里不出来了?”
“嗯!”
常遇春望着六安城头朱亮祖隐约的身影,道:
“这厮要么已经窥破俺的计策,要么是上一战吃到了苦头,吓破了胆,不敢再伸头了。用计不成,那就硬啃!先回营,多打造一些攻城器械。俺还不信了,治不了这只缩头乌龟!”
一想到接下来可能是枯燥的长期围城,骑兵没了用武之地,冯国胜顿时没了精神,懊恼地嘟囔: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在舒城分兵时,俺就该豁出去求求元帅,让俺跟着常大哥你一起来打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