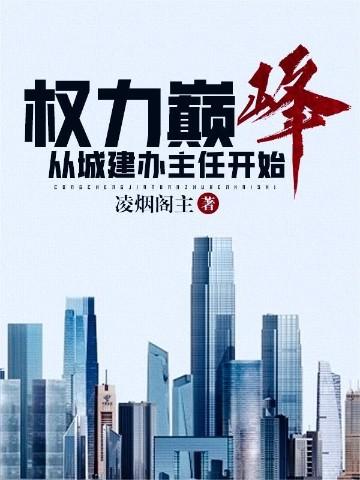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在线阅读 > 第174章 常遇春罕逢敌手(第2页)
第174章 常遇春罕逢敌手(第2页)
他深知自己在红旗营的处境和价值,石山以雷霆手段清算旧势力时,周昶不仅没有为任何故旧同僚求情,反而表现得异常积极,主动提供名单罪证,配合查抄,甚至亲自监刑。
这份“大义灭亲”的姿态,虽然令城中某些人齿冷,却实实在在地为石山省却了无数麻烦和可能的反弹,也为周昶赢得了一个“顾全大局”的评价。
石山心中明镜一般:这是周昶的投名状,也是他立足庐江的资本。
如此又过了六天,常遇春飞马入庐江,传回了先锋部队已克舒城的捷报,庐江军政要务也初步理顺,城中守旧势力遭遇重大打击,余者再想翻身也难。
时机已至,石山决定挥师西进,亲临舒城坐镇。临行前,他特意召见了周昶。
“营方公(周昶表字),舒城捷报已至,我军大胜。明日一早,我便率捧月卫主力西进舒城。这庐江重地,就托付给你了。望你与韩镇抚同心协力,确保此地无虞。”
石山越是尊重,周昶的姿态便越是谦卑。他深深一揖,声音沉稳:
“元帅放心。下官定当竭尽全力,辅佐韩镇抚,守好庐江,静候元帅凯旋!”
周昶话语中韩镇抚,就是韩成。
当初在灵璧,石山只是付出了一担粮食,便让韩成带着众多乡党,跋涉数百里前来投效。
此后,韩成虽然没能像傅友德、胡大海、常遇春、徐达等人那般光芒四射,却也一步一个脚印,在历次战斗中展现了足够的勇毅和忠诚,能力和可靠早已得到袍泽认可。
由这样一位与庐江本地毫无瓜葛,只忠于石山本人的将领来担任镇抚,统管城防军务,是最合适不过的安排,无人敢有异议。
石山对周昶,则是用其才而防其势。
他虽对周昶在庐江的声望和人脉抱有戒心,但此人有能力、有手腕,更难得的是投降后能迅速调整心态,积极配合。只要将其置于韩成的制衡之下,并适时调离其根基之地,便是可用之才。
“营方公。”
石山话锋一转,带着几分嘉许。
“你在庐江抚军民,促生产,平动乱,政绩阖城军民有目共睹。以你之才,长期屈就于一县之地,实非善待贤良之道。待庐江城防体系初步稳固,我便调你入元帅府担任要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周昶已经断了割据一方的念想,却又不甘心告别仕途,自然渴望能在红旗营中攀得更高位置。
石山这个明确的承诺,无疑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坦途。
周昶感激涕零,再次深深作揖,言辞恳切道:
“元帅厚爱,下官感激不尽!元帅挥师征战,正是用人之际。下官长子周耽,虽性情顽劣,不堪大用,却也略通文墨,若元帅不弃,或可为一抄写吏,略尽绵薄之力。”
周昶推荐长子入幕元帅府只是委婉的说法,实则是主动遣送质子。
乱世之中,信义如纸薄。
无论是仇成、夏君祥等半路投靠的义军头领,还是执掌一方军政的红旗营要员,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这条潜规则。
区别只在于,有人心思玲珑,早早将家眷留在濠州大本营;有的比较迟钝,或者暗藏私心,须得“有人”点拨,方才如此做。
唯一的例外,是红旗营内部最大的“杂牌”——合肥军的头领左君弼,不算战败被俘的兄长左君美,其家眷仍都在合肥城中。
石山深知扣押质子绝非万全之策,也不可能因此而杜绝属下背叛。
但若连这点防备的姿态都放弃,那无异于纵容某些人在面临抉择时,毫无负担地选择背叛或骑墙。
石山起兵时别无乡党亲族相助,又遭田昌才、柳丰等人背弃,深知自己任何一丝心慈手软,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导致成千上万追随他的将士和百姓付出鲜血的代价。
红旗营的家底还薄,石山不敢赌人性,也赌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