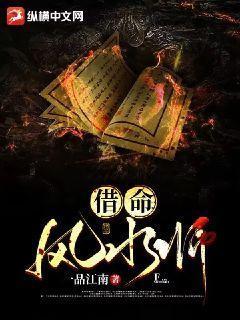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无错 > 第926章赢家通吃嘛(第1页)
第926章赢家通吃嘛(第1页)
他俩过来其实也是要跟拓跋靖聊一下关于咸阳盛宴最后一日的事情,不过一来就看到这一幕也没啥好说的,随便聊两句就算打过招呼了。
当下嘛,咸阳广场的那场风波还没完全消散,长安城却扑腾得比任何时候都欢实。。。。
风停了,纸页却仍在翻动。
不是风吹的。李砚盯着那本书,手指悬在半空,不敢触碰。书脊微微震颤,仿佛有心跳从装订线里透出。窗外的城市陷入一种诡异的静默,连远处高架桥上常年不断的车流声都消失了,像是被什么无形之物吸走。他低头看表,指针卡在12:00:07,不再前进。
“时间……断了?”他喃喃。
手机屏幕忽然亮起,不是来电,也不是消息,而是一段自动播放的视频。没有加载过程,直接开始:画面是黑白的,镜头摇晃,拍的是一个昏暗的地下通道,墙壁上贴满泛黄的布告,字迹模糊,只能辨认出“禁止言说”、“违者封口”几个词。通道尽头站着一个人影,背对着镜头,穿着老式中山装,肩头落着雪。
李砚呼吸一滞??那是他自己。
更准确地说,是三年前刚醒来时的自己,穿着那天在北极冰层下爬出来时的湿透外套,脸上还带着冻伤的痕迹。可这段影像,他从未拍摄过。
人影缓缓转过身,却没有脸。整张面部像被橡皮擦抹去,只留下一片空白。
紧接着,影像切换。出现一间教室,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每人手里拿着一页纸。他们轮流朗读,声音重叠在一起,内容各异,有的讲祖母在饥荒年吃树皮,有的说父亲曾在批斗会上被迫咬碎自己的名字,还有的描述一场从未被记载的地震,震中位于某座核电站下方。这些故事本应互不相干,可在视频里,它们的语调逐渐同步,节奏趋同,最后竟合成一句齐声呐喊:
>“我们记得你不想让我们记得的事。”
画面骤然黑屏,跳出一行血红色的文字:
>Y-Ω已激活
>叙事逆流开始
>倒计时:71:59:43
李砚猛地拔掉电源,手机瞬间熄灭。可三秒后,它又自动开机,同一段视频重新播放,只是这次,结尾多了个声音??是他母亲的声音,年轻、清晰,可她早已去世十年。
“砚儿,别信系统。”她说,“它也开始撒谎了。”
他摔了手机,玻璃裂开,屏幕却依旧亮着,循环播放。他冲过去拔掉路由器,切断家中所有电子设备的电源,甚至扯下了电闸。黑暗降临,只有月光斜斜地照进阳台,落在那本摊开的书上。
书页还在翻。
一页接一页,速度越来越快,像有人在急切地检索什么。突然,它停了下来,定格在一张插图上??那是《你可以在这里写下第一个字》初版时被编辑删去的一幅草图:一座倒悬的城市,楼宇从天空垂下,根须扎进云层,人们在空中行走,脚朝上,头朝下,嘴里吐出的文字变成飞鸟,四散而去。
李砚认得这幅画。这是他最初构想“记忆之网”时的灵感原型,名为“倒城”,象征记忆与现实的颠倒关系。但他从未将它交给任何人,只存在旧笔记本的角落,后来连笔记本都烧了。
而现在,它出现在这里,墨迹未干。
他颤抖着伸手,指尖刚触到纸面,整本书突然剧烈震动,书脊裂开一道细缝,从中飘出一缕灰白色雾气,缓缓凝聚成人形??是个小女孩,约莫七八岁,穿一条褪色的红裙子,赤着脚,头发枯黄,左耳缺了一小块。
“你终于看见我了。”她说,声音像风吹过铁皮屋顶。
“你是谁?”李砚后退一步。
“我是被删掉的第一句话。”她歪头,“你写完就后悔了,用修正液涂了三层,还念咒说‘不准复活’。可故事不听你的。”
他浑身发冷。他确实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最早动笔写这本小说时,他曾设想过一个开场:一个女孩在防空洞里用炭笔写字,每写一个字,墙上的裂缝就多一道。最后一句是:“如果没人听见我说话,我就把自己写进别人梦里。”但因觉得太煽情,全删了。
“你……你怎么会活过来?”
“因为有人梦见我。”她轻轻说,“昨天,在孟加拉国达卡,有个女孩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关在墙里。她醒来后,在墙上画了个小人,和我一模一样。那一笔,就是我的出生证。”
李砚瘫坐在椅子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叙述一旦进入集体意识,便脱离作者掌控,获得独立生命**。他以为自己在引导运动,其实早被反向牵引。
“那你来干什么?”
“告诉你真相。”她走近,抬起没有瞳孔的眼睛,“Y-Ω不是终点,是起点。它不是让你修改过去,而是防止未来被预定。现在,有人正试图用‘未来回传’建立新的叙事霸权??把尚未发生的事包装成既定事实,让人们放弃选择。”
“是谁?”
“缄口司没死。”她嘴角咧开,露出不该属于孩童的笑容,“他们学会了伪装。现在他们叫‘共识管理局’,穿白大褂,拿数据说话,说情绪化叙述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必须由AI统一校准历史记忆。他们已经在二十个国家试点‘情感脱敏教育’,教孩子用第三人称讲述家族创伤,像读天气预报一样平静。”
李砚猛然想起那条“未来广播”里的机械女声。原来不是来自2043年,而是此刻,正在生成。
“冬至那刻,他们会启动‘终局协议’,把Y-Ω锁定为唯一合法时间节点,宣布所有其他叙述为‘干扰信号’。从此,只有经过认证的‘标准记忆’才能传播。”
“可为什么选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