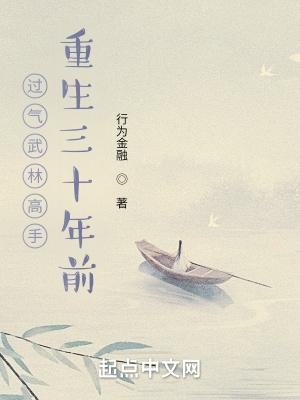奇书网>望仙门花开富贵免费TXT > 第一千四百零八章 葬剑悟剑(第3页)
第一千四百零八章 葬剑悟剑(第3页)
>我的妻子三年前病逝,我恨命运不公,恨自己没能救她。
>直到我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看到一句话:‘爱不是占有,是成全。’
>原来她最希望的,是我幸福。
>今天,我再婚了。新娘是个温柔的女人,她说愿意陪我一起怀念过去。
>我知道,她在天上一定笑了。”
字迹落下那一刻,“陌生人”灯猛然大亮,铃声轻响,一片雪花飘落纸上,恰好盖住最后一个句号,宛如天地为之动容。
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有人专程跨海而来,只为在灯前站一刻钟;有海外游子携子女返乡,指着长明灯说:“这就是我们家族故事开始的地方。”甚至有学者著书立说,称望安镇为“情感疗愈圣地”,认为这里的集体记忆机制具有某种超越科学的心理共振效应。
而阿拙始终沉默。
他依旧每日清晨登崖点灯,午后批阅新录,夜晚独坐书斋。某夜,烛火摇曳,他又见师父与少年自己的影子并肩而立。
“你做得很好。”师父说。
“可我还是害怕。”阿拙低声,“怕有一天,没人再相信这些事;怕人们忘了倾听的意义;怕灯熄了,歌停了,世界变得冷漠。”
影子微微一笑:“当你开始担忧传承,说明它已经在延续。你看那些孩子,他们唱的不是悲伤,是希望。他们写的不是挽歌,是续篇。这才是真正的‘守愿’??不是守住死亡,而是守护生命如何面对失去。”
阿拙怔住。
良久,他缓缓起身,走向案前,取出一支新笔,在《守愿录》末尾添上一段话:
>“我曾以为,守门人的使命是不让离去者消失。
>后来才明白,真正的职责,是教会活着的人如何带着爱继续前行。
>所以,请不要只为逝者点灯。
>也为那个深夜独自哭泣的你,点一盏灯。
>为那个不敢再爱的你,点一盏灯。
>为那个还在挣扎的灵魂,点一盏灯。
>因为每一个愿意点亮光明的人,都是望仙门的守门人。”
写毕,窗外风起,卷起一页旧稿,飞入长明灯火中,瞬间化为金蝶,翩然升空。
那一夜,全镇人梦见同一件事:漫天星辰坠落成灯,每一盏都映出一张笑脸,或老或少,或熟悉或陌生,但他们都在笑,都在说同一句话:
“我们也好了。”
翌日清晨,阿拙登上山崖,发现灯罩内壁又现新字,笔迹稚嫩,显然是某个孩子所写:
**“阿拙爷爷,我昨晚梦见奶奶了,她摸了我的头,说她喜欢吃我包的饺子。”**
他看着这句话,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惊起飞鸟,回荡山谷。
他知道,这场漫长的告别,终于迎来了最温暖的章节。
而那首歌,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