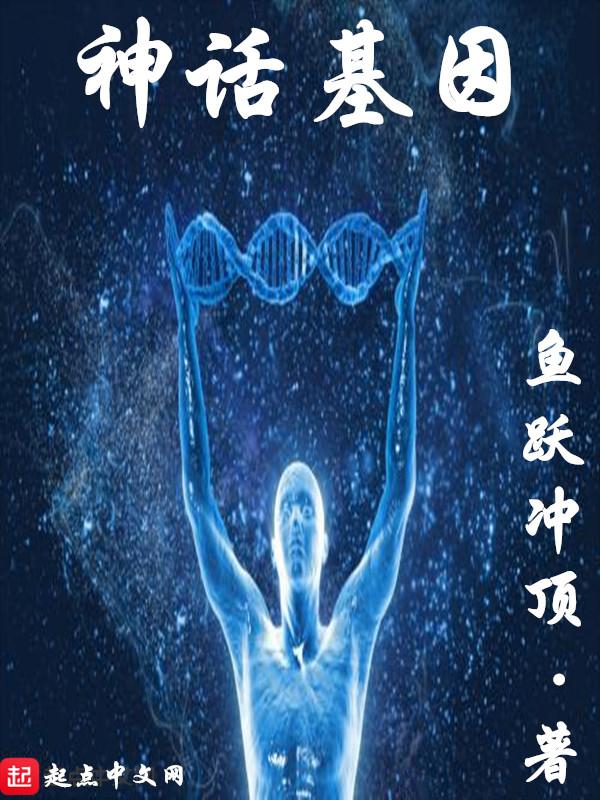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皂角树上的刺有什么作用 > (第2页)
(第2页)
栀子说:“你这话当真!”
皂角朝地上吐口唾沫道:“这东西掉在地上舔不起来!”
栀子的眼圈一下子红了。栀子哭了,哭得很是伤心。
第二天一早,栀子真地走了。皂角赌着一口气,不追也不拦,站在皂角树下运足气地骂:“猫认千狗认万,老母鸡只认二里半,我就睁眼看着你能跑哪里去!”
3天过去了,栀子没回来,30天过去了,栀子仍旧没回来。皂角按不住心口了,他交待铁蛋好好看门不要乱跑,他要出远门去找栀子。他汗淋淋地来到木匠家,栀子果真在这里,话匣子里正播着二胡独奏,高山流水,叮咚有声。皂角说:“栀子,那日我是气话,你回吧!”
栀子说:“不回,我坐在**就听得清话匣子嗷嗷叫。跟你回去做什么?”
皂角说:“卖猪的钱一个没动,豁出去了,我也给你买个话匣子!”
栀子说:“不用蒙我,木匠哥说了,这话匣子是有线的!”
皂角说:“买得起马备得起鞍,有线咱就也给你买线!”
栀子的眼圈就红了:“皂角,你就回去吧!我是王八吃秤铊——铁了心的!你要不嫌隔河渡水,每年皂角树开花时,就把铁蛋领来我看看,咱俩的缘份就这些了!”
皂角呜咽着说:“栀子,就为了那个话匣子,你不要男人也不要儿子了,你好狠心!”栀子看了皂角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一个劲儿用手帕抹眼圈儿,那手帕镶着花边印有鲜红的牡丹花,皂角第一次看见。
金风一遍遍扫落树的叶子,那皂角树枝上的大刀片儿互相撞击着**的身子,发出一片哗哗啦啦地声响。再也没人去打那荚果儿了,小院里荒凉冷落,皂角终于没能说服栀子,栀子终于在龙亢集做了木匠的婆娘。
皂角树上的小黄花又开了七八次。村里的人成群结队地出外打工,铁蛋也跟着走了。屋里空空落落。皂角便有些寂然,见天干一顿湿一顿糊弄肚子,便去田里打草刨茅根,打来的草晒开了,便捆去卖几毛钱换回二两白干酒,就一口咸菜喝一口辣水儿,蒙上头酣酣地睡,睡着睡着就做梦,梦见皂角树又开小黄花,又结大刀片,梦见打荚果的栀子和她那一围喜人的细腰,免不了心口兀地憋闷,鼾声顿息,快快坐起,皂角就骂自己:浑男人!贱坯子!
又是一个春天来了,院子里那株皂角树在融融的春阳中悄悄抽出许多新枝,朦胧的绿如一层淡淡的雾。那一天忽然风传,有人给村里的光棍汉领来了几个江苏小蛮子。皂角心动不已,栀子走后,他想过再讨个老婆,可是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找对象都难,何况他还带个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便渐渐灭了非念。现在儿子走了,出来进去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也没有,皂角不老,他想碰碰运气。
他刚打听便失望了,小蛮子全都有了主儿,且年龄又小太不般配。夏天的时候,有个小蛮子的寡母来看女儿,在村子住了几日,见吃穿都像是过日子的人家,便提出想落户,无奈女婿是个小气鬼,人前背后不赏好脸色,老蛮子不敢在家里闲坐,就天天下地拔草。
中午头拔晒草是村里人的习惯,皂角也不例外,因此时常碰上老蛮子,碰上便搭讪拉呱儿,先拉吃啦喝啦大众话,后拉命啦苦啦体己话,拉着拉着二人都生出了同病相怜的滋味儿,老蛮子说你也真不容易,皂角说你也真够苦的。只顾叙话常忘了薅草,每当要走了,皂角便把自己筐里的草一股脑儿都塞进了老蛮子筐里,并且说:“没人管我的,我不在乎!”
老蛮子不老,四十出头大脚板细腰杆,江浙女子肤色好,白白净净挺受看。一天中午,太阳像泼火,皂角在家热得吃不下饭,便去村北大甲沟里洗澡,刚脱光衣服下水,便听见不远处的蒲丛里有响动,别是水鬼吧?皂角有点迷信。他蹲下身子仔细地瞧去,哟!差一点没晕过去,碧绿的蒲丛里,两只丰满的奶子斑斑驳驳地闪来闪去,那茭白似的肌肤,那细长的身段,那根把瀑布似的黑发卷成喜鹊尾巴在阳光下闪耀着刺目金光的大发卡。
原来这天中午,老蛮子在女儿家豆地拔草,实在热得眼发黑,看看四周寂静无人影,就脱了衣服跳进大甲溪的蒲丛,这女人肩能挑,脚能走,洗澡也特别的讲究,先扬湿了全身,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擦,就象在精心塑一座雕像。老蛮子洗得认真,皂角看得出神,看着看着,灵魂出窍,竟有了腹疼胸堵之感,他恶狠狠地骂了句“贱坯子”,就忽地钻入水中一个猛子扎了过去。蒲丛里一阵刷的**。皂角便有了十几年来第一次天崩地裂地快感。横七竖八揉成一团的蒲丛上,抖如筛糠的老蛮子双眼充满了恐惧。嘴唇不住地颤抖,皂角笨拙的双臂铁钩一般地搂紧了那茭白似的身子。他咬着老蛮子的耳朵连说:“别怕!我娶你,我会娶你的,今晚你就搬到我家来,听到了吗?”老蛮子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皂角又说:“我会让你享福,我不再叫你吃苦,明白吗?”老蛮子睁开眼睛又点点头。皂角感动得泪水盈眶,他轻舒猿臂,把个光油油的老蛮子滑腻腻地抱上溪岸,穿上衣服,俩人一前一后,不声不响地进了村。
女人家女人家,没有女人不成家,小院来了个女人,便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黄母鸡红着脸唱着蛋歌,大白鹅悠闲地迈着方步。饭桌上,老蛮子温好老酒,皂角三五盅下肚,便搂过老蛮子说:“老婆听清了,我是天你是地,咱俩合起来好好奔日子。”老蛮子微笑着夹一撮炒韭菜送进皂角嘴里。皂角便血脉畅流惬意无比,皂角很是快乐了一些日子。之后便渐渐有些不对劲了。
老蛮子进门的时候,别的东西都不要,唯独要了一只大木盆和一只马桶。蛮子爱洗,一天绝不漏过。那洗的认真劲儿常让皂角受不了。两个大人吃饱喝足没有事,蓄了精力就想动真的。可是老蛮子吃了晚饭烧好水要坐在木盆里上上下下抹一遍,哗哗啦啦地响了老半天,皂角等不及便骂:“那里面到底有什么脏物,天天抠也抠不净!”老蛮子就应:“快了快了别着急么!”说着快了快了,至少还得等一碗饭功夫。四十出头爱发困,等老蛮子擦好了上床时,劳累一天的皂角困意袭来眼皮好重,骂一声“操!”倒头便沉沉入梦了。
有一天晚上多喝了二两,皂角火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将蛮子从盆里湿淋淋地提出来,扔在**就干,硌得蛮子亲娘妈妈地叫。最叫皂角不能忍受的就是那只马桶了,大白天的蛮子关了门就蹲在马桶里拉屎拉尿,出了院门朝后两步就是茅房,几步远都不肯走吗?一个大人天天在屋里屙尿多寒碜人。端起碗一想起那气味,皂角就想吐。他几次把那只马桶扔出去,却又被蛮子捡了回来,皂角气愤之极打了蛮子一个耳光骂道:“你是一只屎壳螂!外面光滑里面脏!眼见你天天擦的像个人样,尿屎都拉到祖宗的牌位上去了。”
老蛮子委屈地哭了,边哭边说:“我这大年纪,你还打我?”
皂角更气:“馒头再大笼蒸的,年纪再大你也是我老婆,我就怎么打不得?”
“你真不讲理!”老蛮子捂着泪眼跑了,老蛮子跑到女儿家,怎么劝也不愿意回来,不久又回了江苏老家。村里人就说,“皂角还是去江苏找找吧!”皂角说:“找个鸟!老蛮子走了我不悔,我蹶着屁股刨一天的茅根,不够她晚上烧一锅热水,她洗屁股的水比我洗脸的水还讲究,我养不起她!”
皂角又成了一个孤零零的鳏夫。岁月流逝,桑田有变,村子里突然修起了砂石公路,公路径直通到龙亢集,小四轮在公路上突突地跑,有黑烟余音袅袅入青云。皂角做完了责任田里的活计,便乘小四轮跑到龙亢集喝闲酒,一喝喝到红日西沉,依旧坐小四轮回家,常喝常醉,醉了便独自坐在皂角树下叹息。有一次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在煤矿上做临时工的儿子转了正,且找了个俊俏的对象。春天到了,铁蛋来信说,月底该休班,要带小对象来家玩。皂角很是着急,做了公公该拿什么给儿媳当见面礼?想了几天找来了几个邻居,一起动手把院子那棵皂角树挖掉拉到龙亢集卖了。皂角拿着卖树的钱,跑了满街大小商店,认真选了一只大木盆和一台带黄梅戏唱片的留声机。
月底刚到,铁蛋就带着花蝴蝶般的对象回来了。儿媳妇进院门就扬声喊爸,皂角几乎舒坦得晕倒。当着儿子媳妇的面,皂角拎出了那些备好的见面礼。儿媳妇一见便咯咯地笑出了声,铁蛋说:“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吗?”
儿媳妇说:“我们房间有卫生间和浴缸,用不着木盆的!”
皂角说:“那就把这话匣子带去吧!媳妇们都最肯听话匣子的!”
儿媳妇一听笑得更响了:“爸,我们有双卡录音机落地式音厢,用不着什么话匣子,你老爱听就留着你老自己听吧!”儿媳妇不经意的笑刺疼了他,皂角满心的欢喜消失了,他怅然若失地走到院子里,站在那个还未及填平的树坑旁,脑子里就像一团糊涂浆。晚上陪儿子媳妇多喝了几盅,皂角又醉了。儿子扶他去睡觉,他突然睁了睁朦胧的眼睛说:“世上最难弄的就是女人!”
铁蛋听了,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