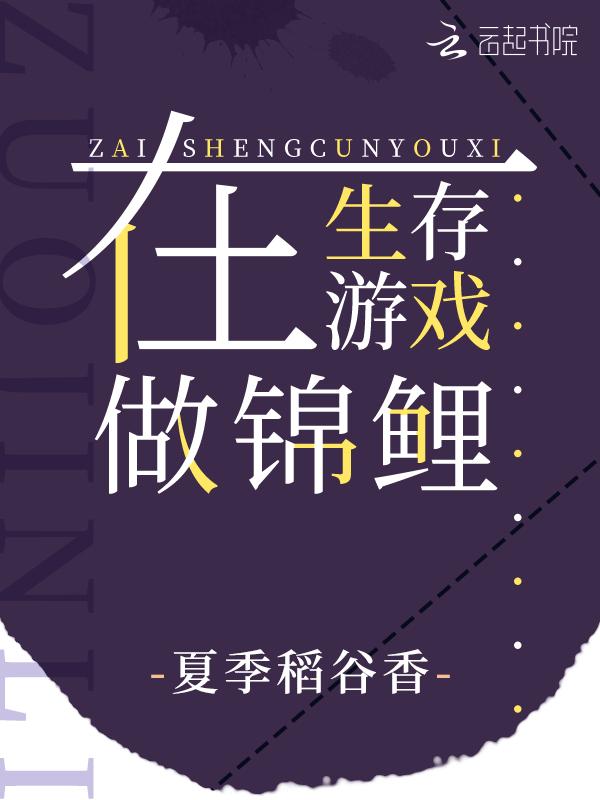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陛下你管这叫没落寒门最新阅读 > 第308章 人微言轻不敢多嘴(第1页)
第308章 人微言轻不敢多嘴(第1页)
杜大友跪在地上,涕泪交加。
从如何被沈安威逼利诱,参与到这贪墨秋粮的勾当之中说起。
他将每一笔账目,每一次分赃,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就像一个溺水之人,拼命地抓住陆明渊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和遗漏。
陆明渊静静地听着,那张年轻得过分的脸上,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那深邃的眼眸,随着杜大友的供述,愈发显得幽冷。
他身后的镇海司堤骑,早已取来笔墨,将杜大友的口供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
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成为了这间牢房里唯一的声响。
待杜大友说完最后一句,整个人已然虚脱,瘫软在地,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陆明渊这才缓缓开口,声音平淡得不带一丝波澜。
“你所说的账本,藏于何处?”
“在……在小人家中卧房的床下,第三块青砖之下,有一个暗格……”
杜大友有气无力地答道。
“很好。”陆明渊点了点头,对身旁的骑士下令。
“陈武。”
“属下在!”
一名身形沉稳的骑士立刻出列。
“你带两个人,持我手令,即刻前往杜大友家中取证。”
“记住,动静要小,切不可惊动了街坊四邻。”
“遵命!”陈武领命,转身快步离去。
陆明渊的目光再次落回杜大友身上,语气稍缓。
“你今日之举,算是戴罪立功。”
“本官说话算话,你的家人,只要未曾参与此事,本官可保他们无虞。”
杜大友闻言,浑浊的双眼中终于泛起一丝光亮,他挣扎着磕头,声音哽咽。
“谢……谢伯爷!谢伯爷大恩!”
陆明渊不再理会他,转身看了一眼瘫在角落里抖个不停的沈安。
陆明渊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
他什么都没说,径直走出了这间牢房。
……
典史吴兴的牢房,比沈安的更加偏僻阴暗。
当牢门打开,陆明渊的身影出现在火光中时。
吴兴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从草堆上弹了起来,畏惧地缩到了墙角。
他不像沈安那般,还有着知县孙智做靠山的虚幻底气。
他只是一个典史,一个在瑞安县官场食物链最底层的角色。
平日里靠着依附沈安和孙智才能作威作福。
如今靠山倒了,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