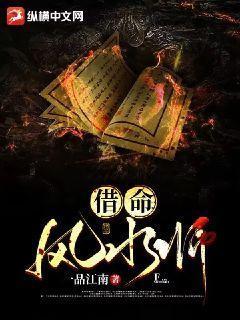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迟延履行金的法律规定 > 第79章(第1页)
第79章(第1页)
厉梨不让他说了,借着被他握着的动作,顺势将他拉过来,吻上他的唇。焦急地,热烈地。
漫天的雪纷飞在他们周身,新年的烟火在天际明灭,在家乡凌晨的街头,他们拥吻。
这座生在西北萧索大地上的西北小城,这个镌刻着他们许多童年痛苦回忆的地方,在此刻,因为这个吻,变得柔软,变得湿润。
爱没有将一切都原谅的能力,却足以抚平生命里那些长久的伤痛,让他们都长成更完整的自己。相互独立许多年,终于又紧紧相依。
吻毕,温慕林牵着他往酒店走,像无数次那样,把他们牵着的手揣在口袋里。
厉梨不禁想,如果小时候温慕林再在饶水市待得久一点,他会不会在英语课上被自己感化,脱下那张小扑克脸,也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小手踹在他的小口袋里。
——来不及想了,没有精力去想了。
因为本就走得很快的温慕林忽然小跑起来,厉梨问他跑急做什么,他不回答。
他不回答,却在进了酒店的电梯以后,就从他的手指开始吻他。
刚刚因为着急去见他,跌倒,而冻红的手指。
“你跑这么急做什么?”温慕林还他一样的话。
厉梨盯着他、他唇边的自己的手,和他沉下来的眼神。张了张口,忽而喉头干涩,说不出话。
被拽进房间时,厉梨已经做好了准备。
决定出门的时候,厉梨就明白会发生什么。成年人的世界,做什么都是你情我愿,厉梨也确实想,因为温慕林确实会,每次都能够让他身体和心灵都舒服。
可是——
这位aaronwen同志却把他带到洗手间,开了凉水,勒令他一边冲水一边搓手。
这位十岁就搬到南方去的人还严肃地跟他,这位在北方长到十八岁的人,科普说:“不可以马上冲热水,不然手会胀起来。”
厉梨无奈得有些想笑,但是看着眉头紧蹙的温慕林,心又软成一片。
“温慕林。”他叫他的名字。
“嗯。”温慕林应了一声,没看他,视线还集中在他手上。
厉梨目光往下移,看到后,喉结不受控地滑动。
所以,这个温慕林到底在忍什么,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忍?自己的手真的这么重要么?自己又不是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在雪地里跌了不到十秒而已,真就这么重要吗?
“温慕林。”
“嗯。”还是不看他。
不开心。厉梨抿了抿唇,靠近他耳畔,唤:“aaron。”
握着他的那双手忽然一个用力,然后厉梨对上温慕林冷欲的眼。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温慕林这样的眼神。
于是变本加厉,厉梨故意蹙眉,倒抽一口气,远离他一些,佯装不悦道:“痛啊。”
温慕林声音很冷,反问:“被冻着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说痛?”
手还在冲着凉水,身体却已经热起来。怎么能乖乖就范,厉梨扬着下巴,反问回去:“我有没有被冻着,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啊?”
在浦东办公室楼梯间被扇了那一巴掌后,温慕林就收敛着自我,确实是变得真诚了,但他本性里的一些美好品质也被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