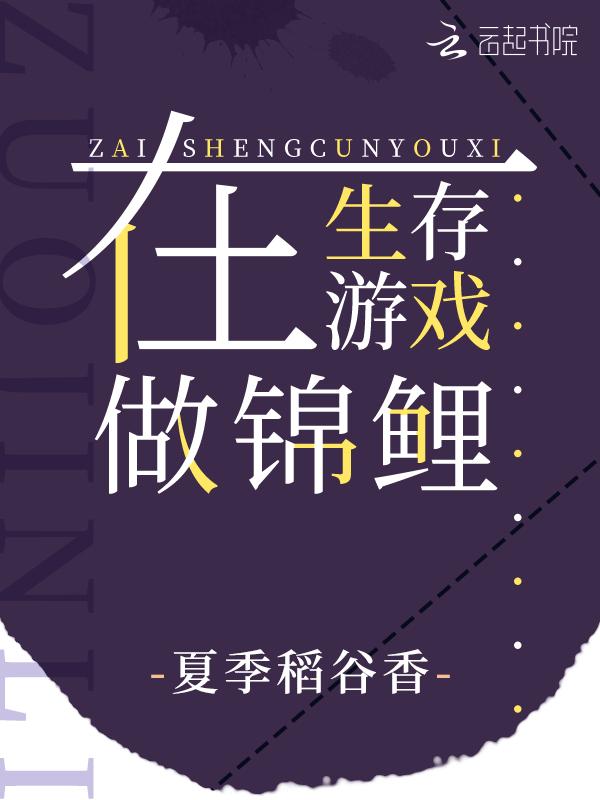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我的月光 > 第八章 最后一只狍子(第1页)
第八章 最后一只狍子(第1页)
第八章最后一只狍子
过去,在我故乡冬天雪白的旷野中,偶尔还能看见有狍子奔跑,它们跃动的影子为旷野边际太阳的红色光轮增添了神性的光辉。可是到了我的父辈,想见到狍子却已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了。
那是一种挣扎在雪白地平线上真诚的生命。我的先辈们称这种可爱的生命为傻狍子。哪个孩子做了愚蠢的事情,大人们就点着孩子憨憨的额头——你这傻狍子!然后绰起预备打狍子的棍向你打来……我们的孩提时代与狍子一样愚蠢悲壮。
多年以后,当我长大成人,刚刚爬出愚蠹悲壮的孩提时代,折身再回到那块雪白的旷野寻找那同我们一样愚蠢悲壮的狍子。
已经没有那种傻狍子了。我爸说。我的父辈们都这么说。
他们淡漠地说,像当年棒打狍子一样淡漠。他们失去的仅仅是味道鲜美的狍肉、温暖抗寒的狍皮。此外,没有别的。我独自在雪白的旷野上走着。我的身后,跟着一簇簇村落,它们顶着雪白的帽子随着我继续向旷野推进。的确,我找不到那种奔跑在旷野上的动物了。
大北方,一旦寒冷来临,我的父辈们就开始了无比闲适的冬天生活,叫做猫冬儿:关上厚厚的门,点上炭火盆,外面着了火也懒得出窝。不过要是谁喊了一句一来狍子了!他们就会鱼贯而出,暂时结束冬眠生活,拎上棒子,冲到冰天雪地里。之后是分狍子肉,亲戚然里,一家一份。慢慢地煮,全村冒烟冒汽,熏燎着结冰的冬天;细细地嚼,寂静村落焕发出生机和芳香。狍皮早已经默默地伏在墙头,一只狍子的形象在悲伤地吮吸着惨淡的阳光。
我在十岁那年翻开了《新华字典》第六百三十页,把狍子那一节中肉可食,毛皮可做褥垫或制革这一行残忍的文字用铅笔抹掉了。我一遍一遍地抹着,黛色一层层浓重,可就是不能彻底盖住这行为狍子带来悲惨遭遇的说明。那一年,我树立了一个不大不小但备受老师赞赏的理想——重编一本字典。坦白地讲,许多年以后的今天,这本字典还没有问世。我时时为孩提时代崇高理想的落空慨叹不已。我如何面对过去的伙伴呢?我跟他们说过,要编那样一本字典的。特别是祥。
坐在雪白旷野中各自的冰车上,我为了美好的计划热血沸腾,忘记了身边严酷的冬天。
故事大略就是从这地方开始的。
这些故事都是那只生着三杈角的狍子引起的。当然,同时这是一个冬天里的故事,白白的雪,略有起伏但尚可视为平坦的旷野。雪来自天上,随意落在起伏的旷野上,但很均匀。这就是这故事的背景,简洁明了。在起伏的旷野上行走,能看见一排蹄印,随着雪白旷野的起起伏伏延伸出去。仔细一看,这就是狍子,那只三杈角的狍子留在旷野上的印迹。这一行远去的印迹让单调的旷野增加了诗意,也增加了大北方冬天的诗意。
它第一次出现,是在我家栅栏外面的谷草垛旁边。它从遥远的旷野尽头跑来,惊奇地句栅栏内的院落张望着,然后开始香香地咀嚼谷草垛上的谷草。
狍子!我爸翻身坐起,从炕头跳了下去,踢翻了炭火盆。那时我还没明白发牛了什么事,只是意识到,这是我爸在这个闲静冬天里的第一个激动的表现。以前他只是围着炭火盆闲静地烤火,用柳条翻里面滚烫的土豆。我爸盘算好了,明年春忙一过就新盖一幢房子。我爸曾神奇地向我透露,房子就盖在旷野的边缘。
村落在向旷野里疯长。
我爸从门后拎出一根木棍,一脚踹开门冲了出去。屋顶上抖落下一些粉末,不是灰尘,是霜,是隐藏在屋脊里的冬天。
狍子发现了来势汹汹的我爸,但它没有立刻明白即将发生什么。它新奇的目光迎向扑来的我爸。它把我爸看成了淳朴善良的大爷。
换了狐狸,早就逃了。可是它实在太单纯了,不懂得这个胃白纯净的旷野中能发生复杂的事情。
可是,木棍不打折扣地落了下来。狍子意识到一些不妙,腾地闪开了几步,但并没有跑开,还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爸。在它看来,这一切太小可理解了。它大概还不愿意相信这个大爷的恶意。
另一记重棍还是落了下来。这回它坚决地跳开了,跑得远远的,消失在旷野中。那时我已经跑出屋子,呆呆地站在栅栏旁,看见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爸掂了掂手中的木棍。两下没打中,他以为木棍出了毛病。我看着他,感到他很陌生。
傻狍子,回去!还傻冻着千什么我爸向我挥了挥棍子。
我灰溜溜跟了回去,走进栅栏时我又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栅栏外的旷野。我希望雪白的旷野中能有一个黑点儿。旷野寂静,雪白雪白。没有声音,没有杂质。
狍子就在旷野上的哪个地方。一定的!
晚上,我爸也这么说,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我爸喝了酒,踌躇满志的样子。陪着我爸喝酒的还有二叔三叔。他们都是闻风而来的,合伙打狍子是一件兴奋无比的事情。喝到兴头上,我爸又绰起那根木棍,比画了两下。我爸说,今年打着狍子不吃了,扛到集市卖掉,攒足钱明年盖房子。狍子肉香,狍子皮暖和!二叔三叔吵嚷开了。真的吗?我拽了拽二叔的衣角,问。那时我还是个无知的小孩,父辈们的议论把无知的我引向了歧途,狍子是一种有用的动物。有用。吃肉。做皮垫子。值钱。盖房子。我琢磨着。
我站在栅栏外面向旷野中张望着。我希望旷野中能出现一个黑点儿,那一定是狍子。我特别希望它出现,说不清为什么。但肯定不是因为它有用。
夜里又扬了场雪。雪漫住了狍子逃走时留下的蹄印。本来我爸他们已经准备出发了,但望了望新鲜的雪,没有进入旷野。他们说,雪又加厚了,狍子找不到吃的,还会跑进村子,那么就不愁打不着狍子;狍子是成群的,就不愁打不着两只三只。我对父辈们的精明惊诧不已。
为了我的冰车,我和祥闹翻了。我背上被撞坏的冰车离开了冰场。冰场上的笑声渐渐离我远去。形单影只,我又想起那只独来独往的狍子,它一定也已失去了伙伴……我踏上了旷野。
原谅我。祥跟了上来。
这事怪祥。祥的冰车从后面撞坏了我的冰车。冰刀要掉下来了,不钉一下就不能玩了。那样,整个冬天就要白白交待了。
我爸发现了狍子。他一定能打住它。我没理会祥,只顾说着自己想说的话。我认为这是对祥的一种蔑视。什么?狍子……祥又从背后跟了上来。对,狍子。它跑进旷野了。不过它跑不掉。我重复了刚才的话。这时我把那狍子想像成了祥。
祥听罢显得特别激动,冰车掀落在雪地上。你们要杀狍子?祥问。对。我望着起伏的旷野,没有看祥。你……狍子是善良的动物。人们在野外冻麻了身子,遇上狍子,它会舔醒你,还把皮毛贴在人身上……爷爷讲的。祥讲了他爷爷民国二十一年的经历。祥的爷爷穿过大旷野,到镇上跑买卖,途中遇见了胡子就是土匪。胡子搜去了爷爷身上的大洋,还扒走了爷爷身卜。的羊皮袄,然后把爷爷扔在旷野中,打马而去。那是冬天的早晨,爷爷的腿受了枪伤,倒在雪地上渐渐失去了知觉。嗒嗒声从旷野深处传来,不久一股暖流**遍了爷爷的全身。一群觅食的狍子救了祥的爷爷……
不知不觉中,我的冰车掀落在雪地上,扑嗒声在旷野上回**。
善良的狍子!原来是这样。
那,咱们应该帮帮那狍子……我呢喃着。我彻底忘记了刚才在冰场上跟祥发生的不愉快。
大雪再度加厚了,旷野更加苍茫。我爸一挥木棍,断定:狍子就要出现了。
我爸、二叔、三叔各自拎着棍子守候在屋里,死死盯住窗外。栅栏外,那垛金黄的谷草上面换了一顶厚厚的白帽子,特别好看。这是诱引狍子的天然饵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