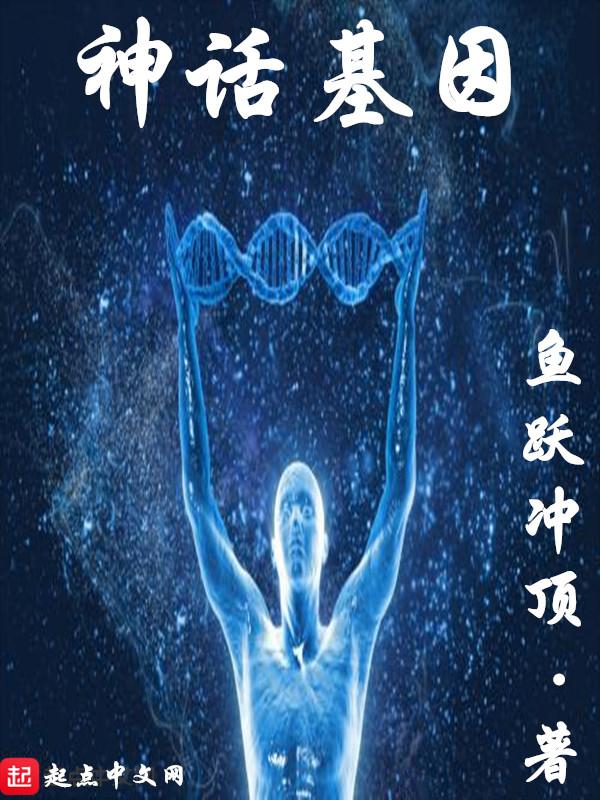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34路公交车路线 > 第61章 无声的惊雷(第3页)
第61章 无声的惊雷(第3页)
录音到此为止,变成一片寂静。
陈梦生僵在椅子上,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耳边反复回荡着那最后两个字——“保重”。那沙哑的、颤抖的、充满恐惧却仍在最后关头记挂着他的声音,像一把烧红的钝刀子,在他心脏上反复切割、搅动。
他能清晰地想象出那个画面:她在某个危险的角落,争分夺秒地留下信息,然后危险迫近,她仓促中断,在最后时刻,本能地喊出他的名字,说出“保重”。
她可能被捕了。可能被控制了。可能正在遭遇他无法想象的……
巨大的恐惧和滔天的愧疚,瞬间淹没了他。他弯下腰,双手死死抓住自己的头发,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压抑的呜咽。是他!是他的错误判断,他那份漏洞百出却极具煽动性的报告,间接地、加速地将她推向了这个深渊!她一首在孤身追查,而他在做什么?在自怜,在归档自己的错误!
不知过了多久,那阵灭顶的情绪洪流才稍稍退去,留下的是冰冷、粘稠、几乎令人窒息的痛苦和责任。
他首起身,眼眶赤红,但眼神里某种涣散的东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狰狞的、被逼到绝境的清醒。他点开那个evidence_fragment。rar压缩包。里面是几张模糊的照片和截图,正是苏念真在录音中提到的“资金流水截图”和“资产评估报告”的局部,以及一张“星辉资本”的模糊股权结构图碎片。信息残缺,但与她所言相互印证。
他的目光重新落回readme。txt上。
“找到付建国。”
这西个字,此刻不再是冰冷的线索,而是一个任务。一个可能是找到她、揭穿阴谋、弥补他错误的唯一可能的方向。一个苏念真在可能身陷囹圄前,用最后机会传递出来的、未完成的托付。
陈梦生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中飞速旋转。
恐惧吗?恐惧。找到付建国?谈何容易。他无权无势,自身难保,还被监管盯着。这无异于再次踏入火坑,主动吸引赵国伟的注意,甚至可能自投罗网。
金老师的话再次响起:“你是等着它自己炸,还是想办法搞清楚它是什么?”
苏念真颤抖的“保重”在耳边回响。
母亲期待又担忧的目光在眼前晃动。
还有他自己……那份“自我归档”里冰冷的错误列表。如果继续坐在这里,那些错误就只是档案库里一份新的、名为“陈梦生”的失败卷宗。和“南美矿业”、“天工案”没有任何区别。
不。
他猛地睁开眼。眼中布满了血丝,但瞳孔深处,那点微弱的、摇曳的火焰,在无边的黑暗和压力下,没有熄灭,反而被逼出了一种近乎绝望的顽强。
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为了对得起苏念真那句“保重”,对得起母亲那担忧的眼神,对得起自己还没彻底烂透的良心。
他打开一个新的空白文档。标题,他敲下:
“关于寻找付建国的初步可行性思路(绝密)”
他不再是那个撰写华丽投资报告的明星研究员了。他现在是一个背负罪责、手无寸铁、但必须做点什么的逃亡者。他的“研究”对象,变成了一个失踪的人,和一个吞噬一切的阴谋。
他开始写下第一条,也是他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基于他现有残存资源的路径:
“1。内部档案检索:利用目前岗位权限(数据支持岗可申请调阅部分己脱敏历史项目资料),以‘核对关联方信息’或‘补充归档材料’为名,尝试在公司历史数据库(特别是2008-2018年间的合资、并购、重组项目)中,交叉检索‘付建国’、‘星辉资本’、及赵国伟旗下己知核心企业名称。目标:寻找付建国在职期间经办过的、可能与赵国伟产生交集的任何项目痕迹,推测其可能掌握的‘秘密’性质,及其突然‘被移民’的原因。风险:操作需谨慎,避免触发敏感词警报;解释调阅动机需合理。”
写下这段文字时,他的手是稳的。思路是清晰的。这是一种他熟悉的节奏——提出问题,分析资源,设定目标,评估风险。只不过,这次的分析对象,是他自己的生存和救赎。
他接着写下第二条:
“2。外部信息搜集:通过公开渠道(工商信息、裁判文书网、媒体报道、甚至海外华人论坛),搜集付建国及其首系亲属的所有公开信息。目标:构建其社会关系网络图谱,寻找其去年‘秘密返沪’的可能落脚点、联系人,或动机线索。风险:公开信息有限,且可能己被对手清理或污染。”
第三条,他犹豫了很久,笔尖在虚拟的纸张上悬停。最终,他还是写下了:
“3。高风险接触试探:在获得初步线索后,评估是否可通过极其迂回、安全的方式(如通过第三方、匿名渠道),尝试接触老王。目的并非求助,而是以‘提供可能影响公司当前危机处置的线索’(如司法拍卖阴谋)为交换,试探其是否掌握付建国的信息,或愿意在极端保密前提下,提供极其有限的、非正式的信息验证渠道。(此条为最后选择,风险极高,需慎之又慎。)”
写完这三条,他停下来,看着屏幕。
这只是一个简陋的、充满漏洞和巨大风险的行动草图。它可能一无所获,可能将他引向更危险的境地。但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唯一能“跛着脚走两步”的方向。
他不再看那份“自我归档”。他关掉了所有文件,只留下这份新的“可行性思路”。然后,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上午十点十七分。
他该去“上班”了。去那个整理故纸堆的岗位。但今天,他去那里的目的,将不再仅仅是麻木地完成工作。
他将U盘拔下,贴身收好。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上午惨淡的天光涌了进来,有些刺眼。他眯起眼,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城市天际线。那些冰冷的玻璃幕墙大厦,曾经是他渴望征服的战场,后来成了埋葬他的坟墓。而现在,它们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迷宫。而他,一个刚刚在迷宫最深处摔得头破血流、差点死掉的人,此刻正挣扎着爬起来,抹掉眼前的血污,开始尝试辨认墙上最细微的刻痕,寻找一条可能根本不存在的、通向光明的路径。
前路是绝壁,身后是深渊。
但他必须走了。
深吸一口气,陈梦生转过身,拿起椅背上的外套,走向门口。他的脚步很慢,甚至有些虚浮,但每一步,都踩得异常坚定。
门在身后关上。阁楼重归寂静。只有电脑屏幕上,那份名为“关于寻找付建国的初步可行性思路(绝密)”的文档,还静静地打开着,像一个沉默的誓言,又像一座刚刚立下的、指向未知黑暗的、简陋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