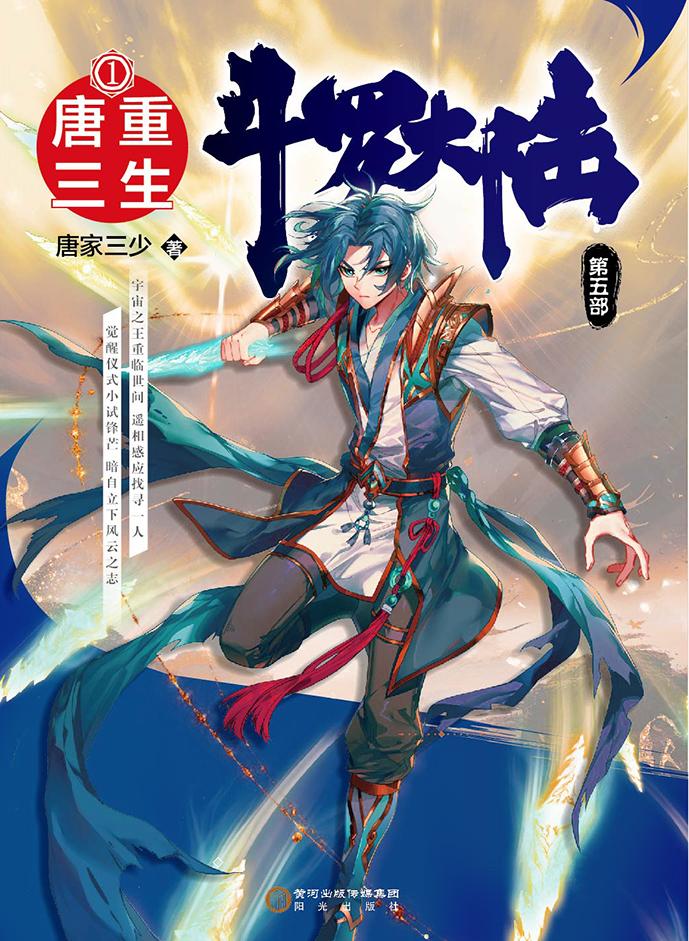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变成男神怎么办啊!免费阅读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沈栖昏昏沉沉地躺着,眼前一阵阵发黑,恍惚间,他好像听到房门被推开的声音,有人把手贴在他滚烫的额头上。
“程言昼,是你吗?”
没有回应。
沈栖费力地睁开眼,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窗帘被风吹起的弧度。
幻觉。
他自嘲地笑了笑,摸到手机想给喻安打个电话求安慰,却在解锁时看到一条未读消息:
【医生十分钟后到】
发消息的人正是程言昼。
时间显示是一个多小时前。
沈栖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觉得鼻子发酸,心里也发酸。
他该高兴吗?
程言昼至少还记着他生病的事。
可为什么为什么连好好关心一下都不行?连亲自回来看一眼都不愿意?
说到底还是因为不在意罢了。
他一赌气,什么都没回复。
现在他的头脑顿时清醒不少,可能退烧药还是起作用了,他侧头看向窗外,彼时一阵飞鸟正好掠过别墅花园的树尖,引起一阵翅膀拍打和鸟鸣交织的响声。
沈栖静静看着那群鸟儿飞远,消失在远空。
心中一动,他想,该试着把那份感情割舍掉了。
虽然可能不容易,但他会学着去做。
突然之间想通了很多,为什么程言昼明明对自己没感觉还不让自己和他离婚呢?
或许程言昼是在意家族的眼光,或许是他占有欲太强,尽管这种占有欲并不出自喜欢。
但一句话,就像喻安说的那样,“对不起人的是他!”
沈栖不想再这样内耗了。
程言昼,我要放下你。
他在心底暗自道。
程氏集团顶楼,程言昼盯着手机屏幕,指节发白。
他还在因为沈栖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了而感到一丝雀跃,但收到发烧的消息还是忍不住心头发紧。
都怪自己没有把他照顾好,他此时恨不能可以穿越回去,就算把空调温度在往上调几度也好啊。
心早就牵挂在家里那人身上了,可除了通知家庭医生立刻去给他看病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一来现在还不是可以遵从心意大大方方对沈栖好的时候;
二来最近和陈氏制药的合作正是关键时期,工作太忙走不开;
三来……
他摸了摸后颈的腺体。
因为那天晚上差点失控,他不惜吃了医院开的不到迫不得已不能随意吃的强效抑制片,腺体被强行压抑,信息素也暴乱,他不得已划伤自己,让痛觉刺激大脑保持清醒。
现在,腺体还在突突直跳,好在处理过后已经不再渗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