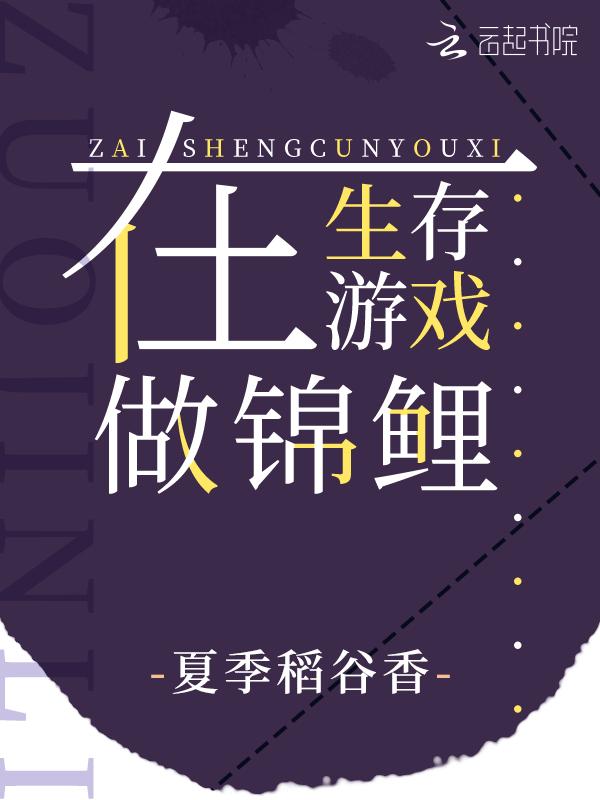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晚清报刊的发展 > 一低下的报人 古典报刊从业者(第1页)
一低下的报人 古典报刊从业者(第1页)
一、低下的报人:古典“报刊”从业者
当《清议报》出版到一百期,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感叹道:“罗马并非一日而成,不过发达之迟缓而无力,独未有中国之报馆者。”[1]梁氏对中国报刊迟迟不能走出古代的窠臼,早有体察。在主笔《时务报》时,这位日后中国的舆论巨子抱怨说:“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2]
在古典思想中寻找西方舶来“技器”的中国渊源或“对应物”,为近代中国流行的一种思维,其中既有面对突然而至的“西方”所流露的自信、自卑交裹情绪,也隐含着为各种变革寻找本土正当性资源的意图。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报刊”远非梁启超所谓的几百年前,胡适在论及《吕氏春秋》所载邓析这位古代“思想界的革命家”时,已经将“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解读为“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3]。实际上“县书”(悬书),即“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与《史记晋世家》等中所载的“悬书宫门”差不多,由于交通枢纽处往来者众多,因此“悬书以示人,故周、秦一时风会也”[4]。这种布告可视为古代中国的一种法令公布方式,对围观百姓而言,则有着教化和命令目的。此后出现的“邸报”,亦是中央集权后行政体系扩展下的产物,这种所谓“报纸”,受众范围更小,功能不过是政权内部的信息传达。
中国古典词汇如“采访”或“新闻”[5],内涵与现代报刊大有差异,区别最大的一点即在于前者多围绕官方展开。古代“采访”指的是采集寻访各类轶事,或用作文学素材,或提供官府考量。例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可视为官员通过民间采集谣谚以了解民情的手段。清代一些地方政府中还有采访局之设,其“职能就是探访、考察民间节妇烈妇一类事迹,汇集至官府以供宣扬表彰”[6]。至于“新闻”,也多源自官方消息的“泄露”,带有相当的猎奇性。[7]
现代报刊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的信息交流媒介,一种非官方社会表达系统,所呈现的是差异和多元事实与观念,而非官方的权威、垄断式真理。以邸报为代表的所谓古代“报刊”,不仅封闭,且消息[8]皆以官方为来源和归依。传统政权为了维护神权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包括日食、地震等异常天象、灾异甚至蝗虫的消息都被禁止在民间传播,如宋神宗之前曾规定蝗灾,须“俟其扑除尽净,方许以闻”。
邸报之谓,只是对官报的一种统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报名称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名确信在唐代已经出现。[9]著名的敦煌《进奏院状》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报纸。[10]时至宋代,城市商业和印刷技术提升,各种貌似“报刊”的印刷物被更多地提及,名称芜杂,如邸状、邸吏状、朝报、塘报、驿报、邸抄,以及京报、京抄、杂报、条报、报状、宫门抄、辕门抄、谕折汇存等,不过多以官方流通为主,内容可视为传统行政信息的传达。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富有活力的宋代,邸报之外的民间“报刊”开始出现,南宋已出现“小报”一词[11],从事者开始为接近信息源和驿运之便的“邸吏”或其他低级文吏,目的一是传递给关系密切的官员,二是试图从中发掘商业机会,由此,民间书肆等印刷产业者也参与其中。此后的明代,报房和抄报行甚至已初具“行业面貌”,主要集中在北京,到明末,北京之外的大城市也有报房出现。清代,民间报房更是集中于北京,他们均自谓“京报”。据估计,北京此类“报刊”每期共发行约一万份。[12]
不过从诞生起,无论是宋代的小报,还是明清的小本、小钞、报条,民间报刊多被政府视为浮言惑众的非法之物。早至南宋,官方已多次禁止“小报”,并出现了“定本”这样的预先审查制度,即只能发行官方审定后的邸报样本,不能超过范围。明末规定,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13]清初甚至一度禁止普通百姓阅读邸报,小抄、小报在乾隆年间也曾遭禁,并发生了新闻史上几次著名的处罚事件:如雍正四年,传报雍正游园细节不实,何遇恩、邵南山被处决;雍正五年,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在奉旨被处斩的前五天,因得见“小抄”而提前自缢。应该说,对信息的控制并非中国独有,而为前现代社会所常见,不过中国尤为突出而已。清代,这种控制由于统治者“异族”身份的不安而进一步强化。
邸报无疑可视为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或政治权力功能的延伸,传播特点在于垂直、纵向,且相对封闭。虽有民间人士喜欢抄录邸报内容做成各种名目的小报,后者也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而更像秘密复制的地下小册子。这种“办报”颇似一种政治偷窥,以满足体制外人士的猎奇心理。由于此前邸报或京报阅读范围主要局限在中上层官员,这种“阅读”无疑充满了神秘感。因为主要围绕邸报等官方信息进行摘抄甚至演绎、编造,民间小报喜欢自称为邸报或京报[14],也不无道理,这些所谓民间“报纸”的出版,操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采访和独立言论。
不能不说中国早期“报刊”从业者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其传统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带有非法色彩的商贩形象,而非“立言”者。南宋,对小报的打击即有“坐获不资之利”之说,明代这一行业虽一度得以公开化,但却以沿街叫卖人的形象示人。戈公振称,传统贩卖朝报或民间小报者多为“塘驿杂役之专业”,他们“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15]。可以说,上述形象成为西方报刊入华前中国社会对报馆从业者的刻板印象。清代的京报虽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只是强化或提升了商业面貌,如北京的多家报房,冠以商业名号诸如聚兴、同顺、同文、兴业,集中于正阳门大街以西的一些胡同里,从业者多为山东人士。直到上海等开埠城市报纸兴起后的较长时间里,办报仍被视为一种不体面的谋生活动。报人作为“送报人”的底层商贩形象,难以抹去。
晚清《东方杂志》对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产生现代报刊,从政治体制上给予如下解释:“中国自古以专制立国者也,士子以闭关自治为宗旨,执政以束缚言论为目的,上下之情惟恐其不壅隔,中外之事惟惧其相过问,斯时固不须有报亦不知所谓报”[16],可谓切中肯綮。事实上,直到庚子事变之前,新式报刊的油墨味虽已在上海的街弄四处飘**,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仍几乎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报刊。彼时的社会环境,“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17]。汪康年创办著名的《中外日报》虽已在更晚的时候,也不由感叹“吾中国人之视报务,素不若西人之重”[18]。报人地位的卑下使得新闻业很长时间被视为“莠民贱业”,以至于戊戌政变后慈禧1898年8月24日所下的谕旨中,还习惯性地称报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虽为污蔑之词,也可见报业与落魄、生活无奈紧密联系的陈腐观念,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用梁启超的观察来说,报人在外界眼里,“形同无赖”,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被看作“固无正当之主意也。旨趣既浅,力亦薄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