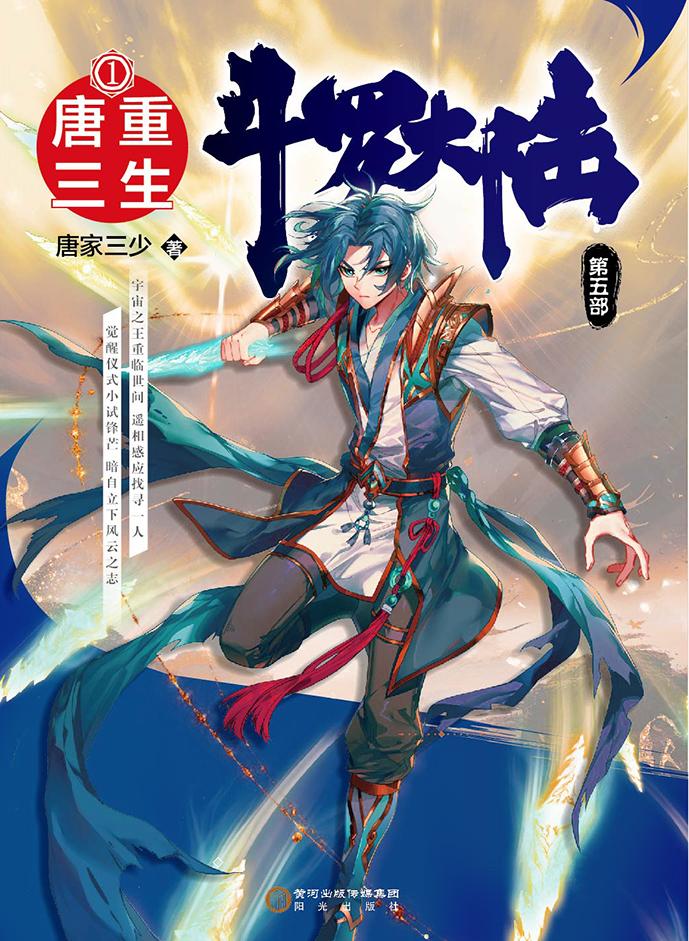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镜像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吗 > 江湖相望(第1页)
江湖相望(第1页)
江湖相望
在《大宗师》中,庄子曾谈到一汪清泉中的两条小鱼。有一天,这泉干了。它们就靠吹气保持对方嘴唇的湿润,靠口中的气泡使对方的身体保持润泽。这种危难时期的相互怜惜,从极微末处写尽了人间的爱与温情。
确实,最感人的往往是最微末的。就像北京的奥运会,若干年后,让人回味的也许不是灼人眼目的烟花,而是志愿者嘴角一抹轻盈而飘逸的笑意。这微笑,是可以牵动记忆的。
但还是庄子,在接下来的言论中却对这种微末而让人震撼的爱给予了坚决的否定。他认为,艰苦时期人性的温情固然美好,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它的美好而留恋这种苦难。为此,他做了个有趣的比较:这可怜的鱼儿“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是值得赞赏的,但与其苦难地相爱着,倒不如在江河的自由游弋中相互遗忘。
庄子是个哲学家,他的许多想法当然比一般人高明。正是这种高明使他凡事都讲超越,也正是都讲超越而使情感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有一次,他的好友惠施问:“圣人固无情乎?”他的回答十分肯定,他的生活实践也好像对他的观点给予了印证。比如,他的妻子死了,他没有哭泣,而是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在他看来,妻子的生命建基于她的形体,她的形体来自于自然之气的凝聚。也就是说,曾经朝夕相处的妻子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股气罢了。这样一还原,当然为一股气哭泣就显得十分好笑。
许多人达不到庄子超越生死爱恨的境界,但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它却表明了理性与情感之间永恒的争执。许多人,既上不了天又触不了地、既渴望超越又未能忘情;大多时候,理性所要拒绝的情感却偏要接受。或者,情感所要接受的理性却偏要拒绝。这就是所谓天人之战。如此,哲学在根本上,就成了人与自身的争执,成了对人生诸种无法克服的欲与情的有关如何克服的论证。
但是,上天创造人,给了人理性也给了人情感。如果这两种对立的力量都来自神的给予,显然它们的存在就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许多人英雄了一辈子,但未能忘情,这种英雄往往被视为有血有肉的人性化的英雄。相反,一些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所谓圣人,反而有点僵尸在世的腐臭味道了。
人总是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游移徘徊的。这种徘徊来自于理性与情感具有不同的指向和功能。比如,陷入情感,就必然会有所爱,有所爱就必然被爱所指向的对象执系或纠缠。前面“陷入”这个词的使用,就意味着情感具有反自由的特质。相反,理性,在本质上是与对象建立距离的,就像我们提醒某人“理性地”思考某一问题时,往往就意味着要让他斩断某种情缘。所以,这两种东西,前者是通过投入对象使边界消失,后者是通过两相隔离建立边界。所以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根本上就是如何看待人与对象之间建立边界的意义问题。
情感在本质上反自由,但它的交互性却保证了相互获得抚慰的可能性。就像河沟里的两条小鱼,这种交互的怜惜十分重要。理性在本质上是守护自由的,但这种守护却极易将守护者守成一座孤岛、一具僵尸,或一个无声无臭的绝缘体。如此,所谓被捍卫的自我,就成了一座自置的牢狱。就像一个环绕自己孜孜不倦的筑墙者,墙筑好了,他也爬不出去了。
如此,在自由与交往、“由自”或“由他”之间,如何取得一种均衡,就显得重要。或者,就像两只刺猬,既要在冬天里相互取暖又要不被对方刺伤,就成了一道巨大的难题。
但不管怎样,庄子式的“相忘江湖”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是以自由的名义彻底遗弃了情感。如此,退一步也许相当不错,即:将“江湖相忘”导致的自我的单体化或牢狱化,恢复为由“江湖相望”产生的张力。
这种张力是重要的。就像童年时期不断扯开又弹回的弹弓,张弛之间,生命变得有趣,变得耐人寻味了。
200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