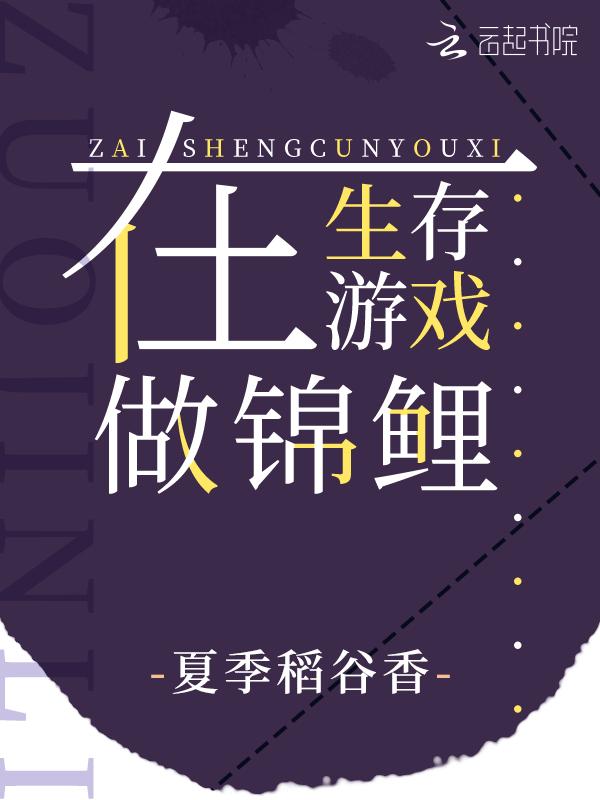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宝贝 > 第29章(第2页)
第29章(第2页)
一楼房间没门锁,梁崇敲敲门,不等里面的人回应,土匪似的推门而入。
床靠墙,床尾立着暗红色大柜子,另一侧的小窗边放有老旧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书桌。
白色网纱状的蚊帐放下来,室内艾草气味的蚊香萦绕,姚今拙从床上撑坐起身,一脸茫然地看向出现在他房间的人。
“你干嘛?”他撩开床帐,探出脑袋。
梁崇:“来睡床底。”
姚今拙又穿着领口过大的旧t恤,短裤被遮住大半,看起来像没穿裤子。
梁崇站在床边,垂眼就看到他颜色很浅,粉色的。
他转开目光,这下是真想睡床底了。
但是床下落了许多灰,姚今拙边骂他有病,边往里挪位置:“滚上来。”
这张床特别旧,最下是层钢丝网,往上铺着层棕垫,然后再是旧棉絮和刚换的新床单。
梁崇坐上去,钢丝网尚还有弹力,床轻微晃了晃。
空调年久,运行声大得像窗外在下雨。姚今拙本来一个人睡下面还有点怕,梁崇来了他安心不少。
空气中多了一股很清新的香水味,像冬日里冰薄荷和雪山。
“老板,”姚今拙凑过去,在梁崇脖颈间嗅了嗅,语气单纯,说出来的话却像骚扰,“你怎么这么香?”
他叫老板,显得两人这时候躺一张床上似是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梁崇心猿意马,耳廓被姚今拙的鼻子不小心蹭了下,呼吸一滞,登时掀开薄毯下床。?
姚今拙问:“去哪儿?”
“喝水。”梁崇头也没回。
真是自作自受。
梁崇打开冰箱,把姚今拙特意冻来放饮料和酒里的一板冰块全敲出来嚼了。
他在厨房坐了二十分钟,估摸姚今拙睡着了才回去,哪知对方根本没睡,还在等他。
梁崇小心翼翼地躺上床,姚今拙忽地翻身,一双眼睛迎着几星碎光,梁崇看见自己占据瞳孔中央。
“你生气了吗?”姚今拙被他刚才的反应搞得摸不清头脑。
喝太多冰水,梁崇此时胃很凉,但姚今拙似乎拥有让水与血液瞬间沸腾的超能力,梁崇没由来地感觉到燥热。
喉结在暗色中滚动了一下,他看姚今拙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片刻后开口说:“没有。”
他说话间带出一丝丝凉意,床小,两人挨得近。姚今拙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伸手碰了碰梁崇的嘴唇。
很凉。
老房子没有隔音可言,梁崇刚刚翻冰箱敲冰块,姚今拙隐约听见个大概。
他不解道:“有这么热?”
空调开得很低了。
梁崇说:“还好。”
“那你去喝冰水?”
梁崇沉默几秒,说:“只是有点焦虑。”
他没说在焦虑什么,姚今拙猜他可能是在担心明年初面试的事儿。毕竟这么早就开始准备,肯定非常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