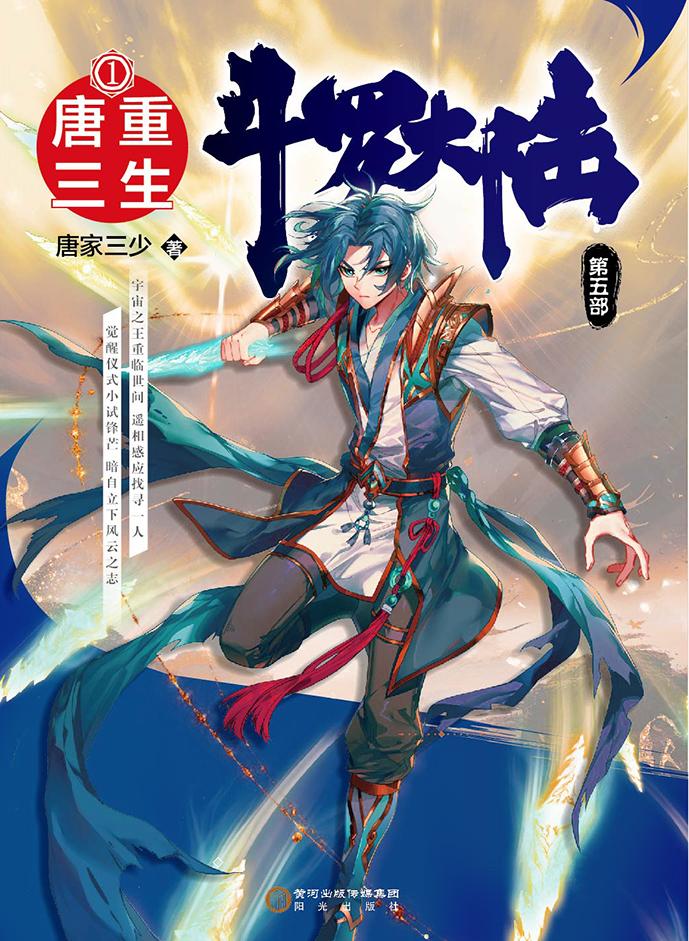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最甜的药物叫什么 > 第4章 出逃(第1页)
第4章 出逃(第1页)
林羡蜷缩在顾连身上,像被抽掉骨头的布娃娃。
起初她只是哭,哭得撕心裂肺,却不敢发出太大声音,怕吵醒顾连,又怕他真的吵不醒他。
可哭着哭着,声音就慢慢低了下去,变成一种近乎气音的、断断续续的抽气。
她盯着顾连那张醉得毫无知觉的脸,忽然觉得陌生得可怕。
这个男人曾经把她锁在房子里、灌药、拍视频、把她当狗一样牵着遛的人,此刻连她被别人按在身边操到失禁,都睁不开眼。
原来连“被顾连占有”都只是她自欺欺人的幻觉。
她连被他珍视的资格都没有。
她更没有被他保护的资格。
名片还黏在她腿间,边缘已经完全被淫水和精液泡软,烫金的“总裁余晟”四个字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着她最后的神经。
她忽然想起以前在顾连怀里发抖时,顾连会一边吻她眼泪一边说:“别怕,你只要当我的小宠物就够了,外面的事老公替你挡。”
原来那句“替你挡”,只是挡到他自己倒台的那一天为止。
林羡慢慢地把脸埋进顾连湿透的衬衫里,闻到一股混着酒气、尿骚味和陌生男人精液的味道。
她忽然干呕了一声,吐出来的却只有酸水。
她想:我到底是谁?
记忆里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过去。
她唯一知道的身份,是“顾连的老婆”。
可现在连这个身份都被剥得干干净净。
她像被抽走了名字的幽灵,赤裸裸地躺在一个废人的身上,腿间还插着另一个男人的名片。
林羡的瞳孔渐渐涣散。
她伸手摸到茶几上的水果刀,指尖抖得几乎握不住。刀刃贴到自己手腕内侧时,她却连按下去的力气都没有。
她只是把刀横在腕上,一下一下地、很轻很轻地划。
没有血,只留下一道道泛白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