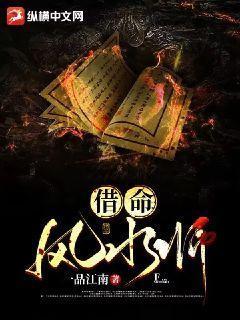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剑来isbn > 第14章 占山为王(第6页)
第14章 占山为王(第6页)
高大男子正是小镇百姓眼中的財神爷吴鳶,窑务督造官,兼任龙泉县首任县令,面对下属们的嘲笑,他也不恼火,坐下后继续先前的话题:“龙泉县衙,文昌阁,武圣庙,城隍庙,四处建筑,光是匾额,零零散散就需要至少十五六块,对於这次驪珠洞天安稳下坠,与大驪版图顺利接壤,维持住了七八分地理全貌,竟然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地牛翻身,陛下龙顏大悦,御赐一块『温故知新匾额给了文昌阁……”
吴鳶说到这里的时候,一个风雅清逸的年轻人微笑道:“吴大人,你就没帮著咱们县衙跟陛下求一份墨宝?”
吴鳶嘆气道:“求啊,怎么不求,可是陛下不答应,我有什么办法。这倒也怨不得陛下,毕竟小小一座县衙,若是得了陛下金笔御赐,让那么多当郡守、做刺史的封疆大吏怎么活?我以后还想不想混官场了?”所有人会心一笑。
吴鳶安慰眾人:“好在刘先生和国子监齐大祭酒分別答应了,到时候会让人送来两套匾额,分別悬掛在县衙和武圣庙,现在问题就在於文昌阁还差三块,城隍庙也缺两块,要不然在座各位,想想法子?难不成真要我自己提笔不成?我那一手蚯蚓爬爬的字,可是连我家先生也感到绝望的。当然,你们不嫌丟人的话,我当然无所谓,这辈子唯一一次將自己墨宝製成榜书匾额的机会,总算到来了!”
那个气质不俗的年轻人想了想:“那我给祖父写一封信去,我家祖父与那位隱世不出的白虬先生关係不错,看能不能想办法给咱们吴大人脸面爭光。”
吴鳶拍了拍他的肩膀:“那本官的脸面就交给你了,要是万一匾额不够,县令大人的脸面就等於丟在地上捡不起来了,到时候唯你是问。”
年轻人脸色一僵,感觉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其余几个岁数相差不大的同僚,纷纷流露出同情神色。咱们这位吴大人,那是出了名的顺杆子往上爬,稍微给点顏色就敢开京城最大的染坊,你敢跟他比拼谁的脸皮更厚?
这些个官气不重的年轻人,身上都有一个在东宝瓶洲北部王朝盛行的官职,秘书郎。这个官职分文武两种,文秘书郎,像是幕僚谋士,为谋主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武秘书郎,就是那两名腰间悬佩金丝佩刀的健硕青年,担任贴身扈从,护卫主官的安全。不过秘书郎一职,属於胥吏阶层,不纳入朝廷的清流正官,世家豪阀子弟出仕,往往由家族聘请或是雇用清客、供奉担任文武秘书郎,当然朝廷也有配发名额,人数从两人到二十人不等,一律可以领取大驪俸禄。吴鳶是寒族出身,私自请不起秘书郎,这些文秘书郎皆是朝廷配给。龙泉县在大驪版图上不过是一个大县,连郡都不是,原本只能配给文武秘书郎各一人,但是那两名金丝缠绕刀鞘的武秘书郎,分明是获得过卓越功勋的大驪军方高手,否则根本没有资格悬佩此刀。其实吴鳶能够出任大驪龙泉县的第一任父母官,就已经能够说明很多问题。年轻县令的授业恩师,是绰號“绣虎”的大驪国师。他的未来老丈人,是在大驪边境沙场戎马半生的某位上柱国。
玩笑之后,吴鳶正色道:“这四座建筑,工程量已经很大,况且神仙坟和老瓷山的选址,小镇这边,从圣人阮师到四姓十族扎堆的福禄街、桃叶巷,很默契地敷衍应付,显然接下来不会顺利,有的磨。但是真正的大事和麻烦事,还是接下来朝廷礼部、钦天监和书院三方將齐聚於此,进行敕封山神河神之事。如果不是山岳正神一事,受到的阻力实在太大,让陛下都有些犹豫,否则连陛下也会御驾亲临我们龙泉县。”
吴鳶看到他们脸色一个比一个凝重,掏出干饼使劲咬了口,轻鬆打趣道:“山岳大神这座大庙,最后能不能建在咱们辖境內的那座披云山上,能不能成为新的大驪北岳,真不是咱们可以掺和的,我们啊,就是县衙里的小鱼小虾,所以別啃著干饼操著中枢大臣的心了,隨那些身著黄紫的官老爷们折腾去。”周围人的心情稍稍好转。
吴鳶默默啃著干饼,犹豫了一下,含糊不清道:“有个消息,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卢氏王朝覆灭后,如何安置那些亡国遗民,一直是个大问题,我们龙泉县接下来会接收五千到一万人的刑徒,鱼龙混杂,三教九流都会有,所以大驪军方会一路严密监督,负责將这拨戴罪之身的刑徒迁徙至此。此举对我们而言,有利有弊,好处是龙泉县终於有点大县的雏形了,坏处嘛,就是乌烟瘴气,让本来就人生地不熟的我们更加无从下手,不得不卖力拉拢那些选择留在小镇的地头蛇。”
世家子出身却当了秘书郎的年轻人问道:“能不能將那些大族分而治之?”
吴鳶毫不犹豫地摇头道:“难。初来乍到,谁愿意相信我们?”
吴鳶沉声道:“与其弄巧成拙,打草惊蛇,还不如慢慢来,来到这个歷史渊源极其复杂的地方,诸位自然是想跟隨我吴鳶一起博取锦绣前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情,大困境下的大磨礪,才能换取大富贵,所以你们谁要是想一两年就升官发財,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掉头走人了,路费我吴鳶帮忙出。”
六个文武秘书郎神色坚毅,无一人有畏难退缩的心思。
吴鳶轻声道:“切记切记,不可急躁行事。”
这绝非是吴鳶说大话空话,而是在进入小镇没多久,他就吃了一个闷亏。当时出动大驪官方势力镇压那个紫烟河练气士,是他吴鳶一意孤行,冒著被朝廷问责的风险,果断地先斩后奏,试图以此打破僵局,先贏得阮师的好感,继而借圣人之势压一压小镇四姓十族。事实证明皇帝陛下那边並未追责,可是当时圣人阮师的反应,却让吴鳶汗流浹背,恨不得使劲扇自己一耳光。
有人好奇问道:“那些遗民刑徒,是用来给练气士们当苦力,帮著开闢荒山的?”
吴鳶点头道:“除此之外,朝廷官方还会让练气士驱使两头年幼搬山猿过来,加上道家符籙派打造的卸岭甲士和墨家巨子打造的开山傀儡,爭取在十年之內,將那六十多座山头全部开闢出来,道观寺庙,亭台楼阁,应有尽有。”
吴鳶身边那些年轻人,全部流露出神往之色。小镇那边,处处平地起高楼,深山之中,多出一座座神仙府邸。所有人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他们作为大驪龙泉县歷史上第一拨官吏,註定会被载入青史,岂敢不勠力同心,不为註定前程远大的主心骨吴鳶效忠效命?
披云山之巔,眉心有痣的清秀少年隨手一挥袖,半山腰的云海被左右拨开,竭力远望,视线尽头,出现了一辆牛车和一辆马车。
他快意笑道:“开赌嘍开赌嘍。齐静春,我要是这一把赌贏了,那么你苦心孤诣留下的两炷香火,就要彻底断绝了啊。可怜可怜。”
少年两根手指拈住一枚印章,篆文为“天下迎春”四个字。
笑眯眯的少年双指骤然发力,印章崩裂,化作齏粉,迅速消散在天地间。之所以如此轻而易举捏碎印章,源於其中四字真意,如人之心灰意冷,失望至极,故而早已自动消散。
少年迅速收回视线,最后看到一个背著箩筐的少年,独自走向小镇。
陈平安出山之后,先去了铁匠铺子,走过那座石拱桥的时候,他双手合十,低头快步而行,神色无比庄重诚恳,碎碎念道:“老神仙有话好好说,千万別打人啊。如果有什么请求,可以晚上託梦给我,最好別大白天的,我是真的有点怕啊。”所幸走到石拱桥那一头,陈平安仍安然无恙,他顿时眉开眼笑,屁顛屁顛去找阮师傅和阮秀。少年不知愁滋味。
阮邛依然是在檐下招待陈平安,一人一张小竹椅,阮秀站在她爹身后,满脸遮掩不住的喜悦。
阮邛看著满身尘土的陈平安,小心翼翼地將箩筐放在身前,又动作轻柔地从大半箩筐草药底下掏出包裹两幅山川形势图的布囊,递给他的时候,愧疚道:“爬挑灯山的时候,山路被一条大瀑布拦住了,我就在瀑布下的深潭附近,找了个地方藏起箩筐,还搭建了一个小树架子遮风挡雨,没想到爬到瀑布顶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雨水实在是太大了,等我赶紧下去,树架子果然已经被压塌了,箩筐和布行囊被雨水浸透,好在两张地图用黄油纸包裹得比较严实,等到太阳出来后,我拿出来看了一下,只是地图边角有些湿,晒乾之后还是有明显的痕跡……”
阮邛打开布囊和黄油纸,发现两幅地图几乎完好无缺,那点折损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再说了,两幅摹本地图而已,所以窑务督造官衙署和龙泉县衙那边,根本就没有要拿回去的意图,但是阮邛可不愿意拿这个真相来安慰陈平安。他瞥了眼站在自己身前局促不安的陈平安,问道:“暴雨时分,在挑灯山的那条龙湫瀑爬上爬下,你找死啊?”
陈平安笑著不说话。
阮邛挥挥手,示意陈平安坐回去,別站在自己身前碍眼。陈平安坐回那张翠绿可爱的小竹椅上,当他把两幅地图送还给阮师傅后,整个人终於如释重负,这一路上如果不是害怕糟践了这两幅珍贵地图,他这趟入山出山至少可以省下三四天时间。而且这么多天相依为命,一向念旧的他其实內心深处,对两幅地图有些不舍。每逢天气晴朗、登高望远的时分,陈平安就喜欢拣选一个视野最开阔的地方,然后摊开那两幅地图,举目远眺看一下山河,收回视线再低头看一下地图。大半个月来,陈平安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
阮邛突然將两幅地图轻轻拋给陈平安:“椅子还不错,回头再做两张,地图就当是报酬了,送给你。”
虽然阮邛还是不喜欢这个泥瓶巷少年,但是他还不至於因此而全盘否定陈平安。
阮邛完全能够想像那幅场景,一场滂沱大雨里,心急如焚的陈平安沿著瀑布往下,只为了看一眼地图才能安心。当然,在阮邛眼中,这种行为一点都没有英雄气概,相反还很刻板迂腐。
说实话,相比这个苦兮兮的陈平安,阮邛更欣赏小小年纪就懂得审时度势的大驪皇子宋集薪,或是生性开朗、万事不愁的刘羡阳,哪怕是锋芒毕露的马苦玄,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就算是自幼跟隨在齐静春身边的读书种子赵繇,也没有陈平安这么死板不开窍。之所以临时改变主意,將地图找个由头送给陈平安,其实是下定决心要跟这个少年划清界限,铁匠铺子可以收纳他作为铸剑学徒,但他绝对不会成为自己的开山弟子,以后自己按照承诺,庇护他买下的山头,但是这小子绝对不要想著跟自己闺女有任何牵连。其实说到底,阮邛並非是因为出身看轻陈平安,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阮邛的徒弟,必须是他的同道中人,双方亦师亦友,能够联手为宗门打造千年盛世,所以性情相合,极为重要。
陈平安自然不知道阮师傅的思绪绕了那么一大圈,他只是接住地图,抱在怀里,问道:“衙署那边督造官大人不会有想法?”
阮邛冷笑道:“至少在六十年之內,我都是这龙泉县的太上皇,所以我的规矩最大。”
阮秀嘀咕道:“爹,哪有你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对於女儿的拆台,阮邛置若罔闻,对陈平安沉声道:“说正事,你最后选中了哪五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