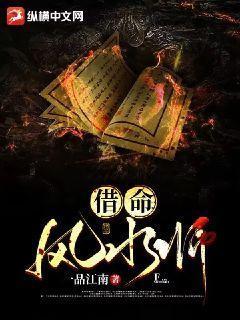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我想听月半小夜曲 > 并发症(第18页)
并发症(第18页)
急救车很快到了,确认好情况后,设置好隔离屏障将沈既白送到急救车内。隗亓明拒绝了是否要同去医院的建议,垂着头站在原地一副不愿沟通的样子。
直到沈既白被紧急转移走,强撑着的隗亓明才瘫坐在地上,失神的双眼落不到实处。他忍受不住地蜷缩起身体,不自觉地咬住自己的手掌,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抵抗其他的疼痛。
生理性的泪水从空洞的双眼流出,悄无声息地落在地板上。雨露仍在时刻不休地纠缠着他,亲亲热热地抚摸着他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
等腺体终于不再剧烈疼痛的时候,隗亓明才慢慢恢复了理智。尖锐的牙齿从几乎要被咬烂的皮肉中离开,沾着令人厌恶的血腥味。
那种钻心的痛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空洞。液体顺着后颈流下,散发着腐烂的花香。
隗亓明不知所措,好半天都不敢伸手去碰。他扶着椅子站起来,晕乎乎地摸出了门。
他不敢大意,打了车往医院去。他已经出现耳鸣症状了,眼前时不时掠过黑影,有好几次都以为自己已经昏迷了。
隗亓明跌跌撞撞往医生办公室走,甫一进门,剧烈的晕眩席卷而来,他不得不伸手扶住门框,好一会才觉得自己回到世界中来。
医生被他的动静吓了一跳,走过去把人扶到椅子上,询问起情况。
隗亓明抖着嘴唇:“腺体……”
医生绕到他背后,轻轻地解下禁锢着的抑制器,表情错愕。
“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
隗亓明若有所感,颤抖的指尖碰上颈后的腺体,倏然僵住。破裂的腺体汩汩地向外流淌着组织液,糜烂的皮肉翻卷着,全然失去了产生信息素的能力。
他的腺体已然坏了,发臭,流脓,一如他死寂的心。
隗亓明睁着眼,一滴泪无知无觉地从眼角滑落:“我会死吗?”
医生放轻了声音:“……会的。”
原来死亡离他这么近,他仿佛又回到了十三岁那年阴湿的湖边,潮湿的水汽裹住他的口鼻,让他几乎哽咽到说不出话。
但他到底还是从湖底逃出来了:“如果把腺体挖掉呢?”
“……挖掉腺体的存活率很低。况且,没有腺体,标记依赖发作的话你也有可能会死。”
隗亓明按住自己颤抖的手,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远处飘过来:“换一个呢?”
“换一个?这……腺体交易是违法的。”
“合法的腺体。”
隗亓明感觉有个陌生人在代替自己说话,要不然他怎么会想起来动用姐姐的腺体?
医生正色:“如果匹配度合适,有可能。”
合适?再合适不过了……若不是被破坏了计划,那枚腺体可能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植入他颈后了。
毕竟,只有在人身上的腺体才更好实验。
隗亓明颓然垂下手。
他明明痛恨着隗芜的残忍,到头来却要依靠他挖出的腺体来求得活着的一丝希望。太讽刺了,兜兜转转他还是没摆脱隗家的影子。
隗亓明闭了闭目,掩饰掉自己眼角的泪。他自言自语似的对医生说:“请给我开一些药吧,我还需要保持正常状态一段时间。”
医生本不想开,但没有药物刺激,损伤的腺体必然会拖垮他的身体。有了药,才有撑下去的希望。
隗亓明如愿拿到了药,足够他去孔家拿回腺体。他不敢跟任何人说明情况,就只在离开前约见了沈既白。
他很有可能活不下来,便想主动把自己从沈既白的生活中抹除。得知消息的沈既白心情复杂,不管怎么纠结,最后还是同意了。
沈既白到的时候,隗亓明已经坐着等了好一会了。下午和煦的日光从透明的玻璃穿过,打在隗亓明俊美苍白的脸上,投射出一小片阴影。他好看的五官在这样的光线下愈发显得夺目,只是这样的温暖却显得隗亓明周遭的气质更冷了。
像一块无法融化的冰。
沈既白轻声在隗亓明对面落座,后者受惊似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很快又垂下视线,好似不想多看见他。
沈既白有些不高兴地抿唇,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坐了许久。
“你还恨我吧?”
良久,隗亓明才微笑着主动开口轻声说道:“以前的事的确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我想补偿你,不过如果没有我,你的生活想必会更好吧。是我自作多情了。”
“……”
沈既白没有言语,低垂着眼帘抿紧了唇,心里隐隐有些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