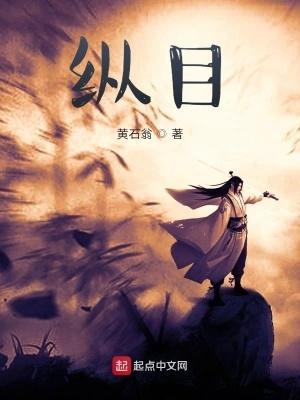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三 星 堆 > 第 27 章(第1页)
第 27 章(第1页)
第二十七章:燕昭明的成长
三星堆的春天总来得热热闹闹。田埂上的油菜花铺成金浪,风一吹就裹着蜜香漫过考古营地,连空气里都飘着活泼的劲儿。燕昭明背着半旧的帆布书包,里面塞着祖父燕守义留下的牛皮笔记本、父亲手绘的古蜀符号图谱,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小学生新华字典》,一蹦一跳地往营地跑。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他也不管,满脑子都是早上母亲说的——今天要清理新发现的小祭祀坑,说不定能见到带符号的陶片。
“昭明,慢点儿跑!莫摔着!”营地门口,老张正搬着一筐工具,见他冲得急,赶紧喊了一声。这孩子跟两年前不一样了,以前总跟在父母屁股后面,怯生生地看队员们干活;现在却像只小麻雀,每天天不亮就往营地钻,连清理文物的小刷子都能耍得有模有样。
燕昭明停下脚步,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张叔,今天真要清理祭祀坑呀?我能去帮忙不?我保证不捣乱,就拿小刷子刷泥土!”他说着,还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小刷子——那是母亲特意给他买的羊毛刷,刷毛软,不会伤着文物。
老张放下筐子,揉了揉他的头:“要得!你燕队和苏姐都点头了,不过得听指挥,不能瞎碰。”他看着燕昭明眼里的光,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山里掏鸟窝的模样,忍不住笑,“你这娃,比你爹小时候还痴迷这些老物件。”
燕昭明没接话,揣着小刷子就往棚屋跑。棚屋里,燕承风正趴在桌上画祭祀坑的剖面图,苏瑶坐在旁边整理陶片残件,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两人身上,暖得像层薄纱。听到脚步声,苏瑶抬头,见是儿子,脸上立刻绽开笑:“昭明来啦?先去洗手,等会儿跟你爹去现场,记得戴手套。”
“晓得了!”燕昭明应着,跑到角落的铜盆边洗手。水是从山涧挑来的,带着点凉,他却洗得格外认真,指甲缝都搓得干干净净——母亲说过,碰文物前必须洗手,不然手上的汗渍会伤着老物件。
燕承风放下铅笔,看着儿子的背影,眼神软下来。这两年,家里出了不少事:穆然的背叛、海外商会的袭击、青幽谷的危机……原本以为这些凶险会吓着孩子,没想到昭明反而更懂事了。去年冬天,燕承风在祭天坡被蒙面人砍伤胳膊,昭明守在床边,用小毛巾给他擦手,小声说:“爹,以后我保护你,我学了好多符号,能看出坏人的痕迹。”那一刻,燕承风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
“在想啥子?”苏瑶递过一杯温水,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昭明,“这娃昨晚还在看你祖父的笔记,问我‘巫首符号为啥要刻在人像底座’,我都惊了,他居然能看懂笔记里的简笔画。”
燕承风接过水杯,喝了一口:“随根。他祖父当年也是这样,七八岁就跟着老守陵人认符号,现在昭明能自己琢磨笔记,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说话间,燕昭明洗好手,戴着小手套跑过来,凑到桌前看剖面图:“爹,这个坑是圆形的,是不是古蜀人的‘祭地坑’呀?我在祖父笔记里看到过,说祭地用圆坑,祭天用方坑。”
燕承风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没错!你咋知道的?”
“笔记里画了图,还写了‘天圆地方’!”燕昭明指着笔记里的简笔画,小手指在纸页上划过,“你看,这里还标了‘陶豆三、玉璧一’,是不是说祭地要放三个陶豆和一个玉璧?”
苏瑶凑过来看,笔记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是燕守义年轻时写的,旁边的图虽然简单,却把坑的形状、器物的位置画得明明白白。“昭明看得真仔细!”她摸了摸儿子的头,“今天清理的坑,说不定真有陶豆,你要是能找到,就算你的第一个‘发现’。”
燕昭明眼睛一亮,攥紧了小刷子:“真的呀?那我们快走吧!”
三人来到新发掘的祭祀坑边时,队员们已经搭好了防雨棚。坑不大,直径也就两米多,深一米左右,坑壁还留着古蜀人挖掘时的痕迹——每隔十厘米就有一道浅槽,是用青铜铲挖出来的。燕承风跳入坑底,铺好塑料布,对上面喊:“昭明,你站在坑边,用小刷子把边缘的泥土扫到簸箕里,莫伸太进去,小心摔着。”
“要得!”燕昭明踮着脚,趴在坑沿上,手里的小刷子轻轻扫过坑壁。泥土是红褐色的,带着三星堆特有的黏性,刷下来的小土块落在簸箕里,发出“沙沙”的轻响。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什么——母亲说的陶豆,是圆肚子、细腿的陶器,他在营地的文物架上见过,要是能亲手找到,多威风呀!
“昭明,慢点儿,莫急。”苏瑶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记录板,“考古讲究‘慢工出细活’,你爹当年清理青铜人像,光底座的泥土就刷了三天。”
燕昭明点点头,放慢了动作。阳光穿过防雨棚的缝隙,落在坑底的泥土上,他突然看到坑壁上有一道浅色的痕迹,不像普通的泥土纹路。“爹,你看这里!”他指着那道痕迹,声音都有些发颤,“这是不是……陶片的边?”
燕承风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泥土里嵌着一点浅灰色的边,边缘还带着弧度。他赶紧凑过去,用竹签轻轻挑开周围的泥土——一片巴掌大的陶片露了出来,上面还带着细密的绳纹,正是古蜀人常用的陶豆残片!
“真是陶豆!”燕承风惊喜地说,“昭明,你立大功了!这是咱们今天找到的第一件完整器物残片。”
队员们也围过来看,小李拍了拍燕昭明的肩膀:“可以呀,小燕!比我们这些老队员还眼尖,以后肯定是考古队的顶梁柱!”
燕昭明脸一红,却把小刷子握得更紧了:“我还要找更多陶片,说不定能拼出完整的陶豆!”
接下来的一上午,燕昭明都守在坑边,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坑壁和坑底。他又找到了两片陶片,一片带弦纹,一片带简单的符号——虽然只是个模糊的“⊕”形,却让燕承风格外惊喜:“这是‘日心’符号,跟青铜人像底座的一样!昭明,你能认出这个符号不?”
燕昭明凑过去看,认真地点头:“我认识!娘教过我,这个符号代表太阳,古蜀人祭地的时候要刻这个,祈求太阳神保佑庄稼丰收。”
苏瑶笑着补充:“没错!而且这个符号刻在陶豆上,说明这陶豆是专门用来祭祀的礼器,比普通的陶豆更珍贵。”
中午吃饭时,燕昭明还在琢磨那片带符号的陶片。他坐在营地的石桌边,捧着陶片看了又看,连碗里的腊肉都忘了夹。燕承风看在眼里,心里暖暖的——自己小时候是被父亲逼着学符号,昭明却是真心喜欢,这种喜欢,比任何督促都管用。
“昭明,吃菜呀。”燕承风夹了块腊肉放在他碗里,“下午我们要给陶片编号,你要不要学?编号要写清楚出土地点、深度、层位,一点都不能错,不然以后就找不到对应的坑了。”
“要学!”燕昭明立刻拿起筷子,扒了一大口饭,“爹,编号用啥子笔呀?是不是那种不会掉色的马克笔?我上次见李哥用的,黑色的,写在陶片上亮亮的。”
“是丙烯笔,不过得先在陶片边缘写,不能写在有纹饰和符号的地方。”苏瑶笑着说,“下午我教你写编号,还要记‘发掘日志’,把今天找到的陶片都记下来,包括颜色、纹饰、尺寸,都要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