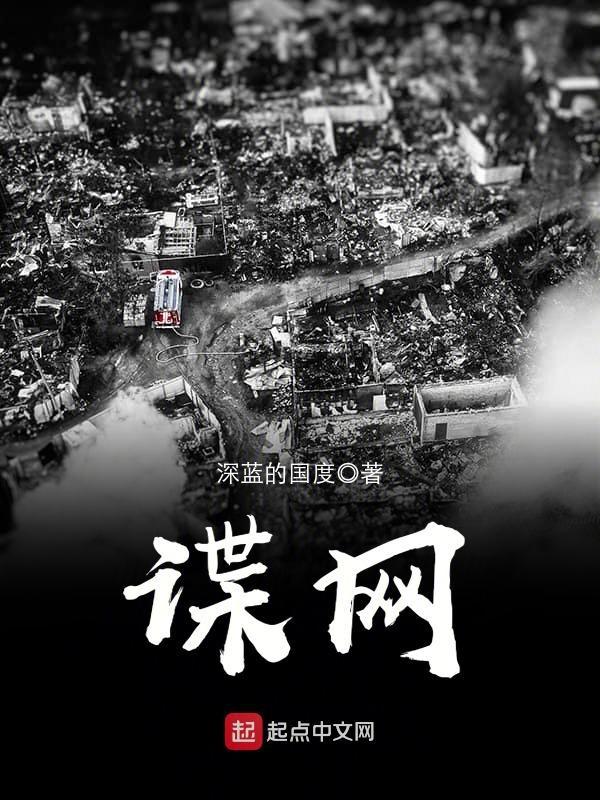奇书网>贞观悍师从教太子逆袭开始全本 > 第197章 恐使刚刚恢复的信用再受打击(第3页)
第197章 恐使刚刚恢复的信用再受打击(第3页)
“届时,损失的不仅是钱粮,更是朝廷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信用,是天下人对朝廷的信心!”
他的语气逐渐加重。
“而若……若能暂缓东征,对内整饬,稳固局势,让这债券体系真正扎根,以逐步充盈国库,潜移默化地增强国力,岂不是更稳妥、更持久之道?”
长孙无忌的眼中闪烁着精光。
他看到了另一条强国之路。
依赖于制度、信用和财富积累的道路。
这条路上,他们这些精通政务、掌控资源的文臣,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所以,齐王之乱引发的债券波动,非是坏事,反而是一个契机。”
他停下脚步,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
“一个让陛下,让朝野上下,都看清‘稳定’和‘信用’何其珍贵的契机。”
接下来的几日,朝堂之上关于高句丽的议题,氛围悄然发生了变化。
当李世民再次召集重臣,商讨在平定李佑之乱后,如何尽快重启东征事宜时,响应者寥寥,且言辞间充满了谨慎。
“陛下,”房玄龄出列,语气一如既往的沉稳。
“齐王叛乱,虽不足虑,然其警示深远。山东之地,门阀势力盘根错节,齐王能骤然发难,亦暴露地方治理或有疏漏。”
“臣以为,当务之急,乃是借平定叛乱之机,彻底整顿山东吏治,安抚民心,稳固后方。”
“若后方未靖而贸然兴大军于外,恐有腹背受敌之虞。”
他没有直接反对东征,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巩固内部,言辞恳切,完全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
紧接着,高士廉也开口道:“房相所言甚是。再者,去岁至今,先有西州开发、山东赈灾,后有债券发行,民间财力已多有动用。”
“若大军东征,钱粮消耗如流水,届时恐物价亦会腾踊,伤及民生根本。”
“还望陛下三思,待国力更充,民心更固,再行东征,亦不为迟。”
他的理由更加具体,直接指向了财政压力和民生负担,同样无可指摘。
李世民的目光扫过长孙无忌,见他垂眸而立,似乎并无发言之意,便主动点名。
“辅机,你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这才缓缓出列,躬身一礼,语气极为恭顺。
“陛下,房相、高公所言,皆老成谋国之言,臣深以为然。”
他先肯定了同僚的意见,然后才道:“陛下东征之志,乃是为解边患,扬我国威,臣等岂有不知?”
“然,《孙子》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他引经据典,将反对的意思包裹在圣贤道理之中。
“今高句丽经我方筹谋,其国内已生乱象,粮草短缺,民心惶惶。此正乃‘伐谋’、‘伐交’之良机。”
“若能暂缓兵锋,持续以盐铁、商贸等手段施压,辅以分化离间,令其内乱不止,国力自耗,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此,既全陛下天威,又省我大唐将士血汗,保全国力以养民生、固信用,岂非上策?”
他句句不离“为国家”“为将士”“为民生”,甚至将李世民的东征意图也包装成“扬国威”,但核心意思明确无比——
反对立刻出兵,主张用非军事手段拖垮高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