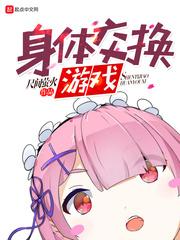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封神 > 碧云(第1页)
碧云(第1页)
在人类意识的幽微深处,想象与思维、幻觉与真实之间,从来不存在泾渭分明的边界。它们更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在意识的土壤里共生共长。想象从不依赖即时的感官馈赠,而是将记忆的碎片、知识的脉络与情感的底色重新编织,构筑出此刻并不存在的景象与声音;而所谓幻觉,有时也并非全然虚妄,它们或许是无意间掀开了世界帷幕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表象之下的另一种真实。
这究竟是意识精心构筑的幻象,还是灵魂在不经意间触碰到的、潜藏在日常之下的真相?杨戬暂时无法给出答案。
当那超越理解的存在缓缓显现时,他残存的理性只能捕捉到一个无比清晰的感受——
美轮美奂。
一种超越了形与色、超越了认知框架的,纯粹而绝对的美。
随后,他眼中的世界开始溶解。万物失去了清晰的轮廓,像墨滴入清水,晕染成一片混沌的迷雾。现实仿佛退到了厚重的帘幕之后,变得遥不可及,不再真实。
静默如潮水般涨起,一浪高过一浪,温柔而不可抗拒地漫过他的脚踝、膝盖、胸膛……要将他彻底拖入那片万籁俱寂的深渊。
他仿佛看见了世界的倒影,那片水面空无一物,平静得如同永恒的安眠。紧接着,这景象猛地碎裂开来,视野化作万千片明亮的残片,又像是无数轮虚幻的月亮,每一片都折射出深沉却又无比明亮的光芒,在意识的虚空中静静悬浮。
有什么东西,正从那世界的倒影深处,缓缓升起。
杨戬的脑海里“轰”的一声,思维的结构瞬间土崩瓦解,再也无法组织成任何有序的念头。成千上万奇异的光与影如星河倾泻,直接灌注到他的意识深处。与此同时,无数个声音——用着他从未听闻却莫名理解的语言,以千差万别的语调与方式——开始在他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呢喃低语。
它们从所有的维度,所有的侧面,同时讲述着各自的故事。
他听见琴弦震颤,流淌出未曾谱写的永恒乐章;他看见诗人未完成的手稿上,浮现出超越语言的优美诗行;他感知到月光下永不落幕的歌舞,满载着最纯粹的欢欣。
它们在讲述故纸堆中尘封的智慧,那些尚未被任何生灵知晓的知识与历史。它们在庆祝——庆祝稻穗低垂的丰收,庆祝生命代代不息的繁衍,庆祝天地间永不枯竭的喜悦,庆祝所有存在那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本能。
这庞大到令人战栗、冗杂到超越理解的信息洪流,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真实”质感,源源不断地冲刷着他摇摇欲坠的自我意识。杨戬的“我”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这片混沌与全知的无垠之海上,承受着一遍又一遍的洗礼,在彻底支离破碎的边缘,载沉载浮。
不知在时间之外漂浮了多久,杨戬的意识才如同沉入深海后又缓缓上浮的微光,一点点重新聚拢。思维的碎片慢慢拼合,感官重新连接上现实,最先恢复的是听觉——或者说,是直接响彻在他灵台深处的声音。
“你……还好吗?”
那声音轻柔得如同月光穿过竹叶的缝隙,优美得像是用露水谱写的旋律,带着一种非人间的澄澈与空灵。
杨戬有些艰难地抬起眼帘。
一个女孩的身影,如同水墨在宣纸上缓缓晕开,逐渐清晰地映入他的视野。
她身着一袭淡紫色的道袍,样式简朴,与各仙家洞府中常见的道童装扮并无二致。然而,某种强烈而独特的气质,却让她与所有他见过的修行者截然不同。
更令杨戬心神为之凝滞的,是她那超越了一切想象与认知的美丽。
在见到女孩容貌时,杨戬近乎失神地想,即便是那些在三界中以美貌著称的仙子,在她面前恐怕也会自惭形秽,掩面而去。
他猛地晃了晃头,试图驱散这种不合时宜的沉迷。心底涌起一阵尖锐的自我斥责——身为修道之人,道心坚定乃是根本,怎可如此轻易地沉溺于一副皮囊表象?这绝非玄门弟子应有的行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与方才那几乎将他意识撕裂的宏大冲击形成了近乎荒诞的割裂。
这是一个非常平淡的来龙去脉,是一个看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的故事。
这个名为碧云的女孩,正是当年被哪吒一箭射死的碧云童子。殒命之后,暂居于这面古镜之中。原本她并不愿与外界,尤其是与杨戬这样身份敏感的阐教弟子有所牵连,只是静观他在洞中徒劳地尝试了数个夜晚。直到想起他此前细心收敛、妥善安葬彩云童子的举动,那份无声的悲悯与尊重,触动了她沉寂已久的心绪,这才决定现身一见。
再往后的事情,当杨戬事后试图细细回溯时,竟发现记忆有些模糊不清。他只记得自己似乎并未多做纠结,便带着那面镜子——或者说,带着寄身于镜中的碧云——踏上了返回玉泉山的归途。
逻辑与理性都在提醒他,这面镜子引发了如此多怪诞离奇的异象,镜中人的身份又牵扯着石矶一脉的旧案,于情于理,他都应当仔细盘问,厘清前因后果。然而,一种源自生命本能最深处的直觉,却在此刻发出了无声而严厉的警告。
那警告并非以言语的形式出现,更像是一阵悄然掠过脊椎的寒意,一种在心脏收缩瞬间捕捉到的悸动。
不要问。
不要深想。
有些真相,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反而是最安全的距离。
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将所有的疑问、所有的探究欲,都强行压制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只是将那面镜子小心收好,如同守护一个不应被惊醒的梦境,默然带着它,回到了熟悉的玉泉山。山门依旧,云雾缭绕,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又仿佛某些看不见的东西,早已悄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