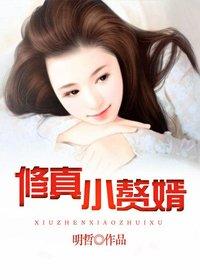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封神第一人 > 凶变1(第1页)
凶变1(第1页)
李玥寰穿过狭窄的街巷,耳畔飘来的不再是“吃了吗”这般朴素的问候,而是一声声带着微妙腔调的——“拜了吗?”
这三个字不再传递关怀,倒像某种暗号,一种对彼此立场的无声确认。
在国师申公豹的引导下,此地信仰正悄然蜕变。
语言对人类心智的塑造力是幽微而深刻的。越来越多的隐喻与特殊用语,如无声的露水般渗入日常。抽象意义被转化为可感知的心智模型,用常人能理解的事物来描述那些不可名状的存在。
这俨然成了一套精密的心智技术。
原本扎根于土地的自然信仰,正被精心修剪成具有严格规范的体系。李玥寰敏锐地察觉到,这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语言改造工程。她想起在现代社会读过的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的地基。当一套特定的词汇系统渗透进日常生活,它就会在无形中重塑使用者的认知模式与价值判断。
卖陶罐的老汉与挑担的货郎在街角相遇。货郎放下担子,抹了把汗,低声道:“今早的‘功课’,可曾圆满?”
老汉慢条斯理地擦拭陶罐上的浮灰,眼皮也不抬:“寅时便已‘奉上心意’。倒是你,这担子里的‘俗物’,怕是要玷污了清净。”寻常的“上香”成了“奉上心意”,日常劳作成了沾染“俗物”。若不使用这套新词汇,仿佛就矮人一截。
每个词语的选择都暗含审视,语调的起伏、眼神的交汇,都在无声地丈量着对方的虔敬程度。
李玥寰在一个枣摊前驻足。摊主是个面色焦黄的妇人,她先快速扫过李玥寰的衣着,才开口:“新到的枣子,沐浴过‘圣烟’的,要尝尝么?”
“圣烟?”李玥寰拿起一颗枣子,色泽与往日并无二致。
“是啊,”妇人压低声音,带着隐秘的得意,“特意在庙门口熏了整夜,沾了灵气的。价钱嘛……自然要贵上两成。”
她紧紧盯着李玥寰的表情,仿佛任何对价格的质疑,都是对那份“灵气”的亵渎。
李玥寰放下枣子,摇了摇头。妇人脸上的热情瞬间褪去,转而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眼神看着她,像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即将被神弃之人。
她转身离开,身后隐约传来妇人与邻摊的低语:“……心不诚,福气自然不会降临。”
这些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宗教用语,就像一块块看不见的砖头,悄悄在人和人之间垒起高墙。它们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说话规矩,把过日子变成了没完没了的信仰考试——吃饭喝水、买卖东西,每件平常事都要被拿来掂量够不够“虔诚”。
最可怕的是,当大家开始习惯用这套话来说话、来想事情的时候,就连“为什么非要这么说”这个问题,都已经问不出口了。
那么,推动这一切变化的申公豹,他究竟在图谋什么?
若说是为了权力,他早已是殷商国师,深得纣王信重,地位尊崇无比。若说是为了摆脱谁的压制,他也并未利用这些信众另立门户,掀起叛乱。
若说是为了财富,这处偏远小国实在贫瘠,即便倾尽国库也搜刮不出多少油水,更谈不上什么值得大动干戈的修炼资源或天材地宝。
李玥寰的指尖无意识地在粗糙的墙面上划过。她想起那间被改建成神庙的破屋,想起里正描述中那户死状凄惨的人家——那些残缺的尸身,那个诡异的自相残杀的现场。
难道,关键藏在那一家人身上?
这个念头如同黑暗中突然擦亮的火柴,短暂地照亮了某个角落,却又很快熄灭。
眼下线索太少,蛛丝马迹散落四处,还串不成一条清晰的线。她站在原地,任凭思绪在迷雾中打转,终究没能理出更确切的头绪。
在这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接触过文字,认知的边界被牢牢锁死在方寸之地。且按照现如今的生产力来看,大多数人都是贫困的,加之脆弱的社会结构无力提供任何缓冲,愚昧则成了最好的培养皿
李玥寰走在日渐冷清的街巷间,目光掠过那些面黄肌瘦的农人。他们颤抖着将最后一把粟米投进功德箱,枯瘦的手指暴露着长期的饥饿。明明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他们却将希望寄托在更虔诚的奉献上,仿佛只要献出最后一口粮,就能换来神明的垂怜。
卖陶罐的老汉近来变了个人。几十年交情的邻居,只因为没按时完成晨间祭拜,就被他拒之门外。在这个越来越封闭的小圈子里,人们互相较着劲,看谁表现得更加虔诚,原本温和的信仰渐渐变了味。
最让李玥寰感到寒意的是那个枣摊妇人。她在摊前挂起自制的符咒,声称能看透来客的诚心。那天,一个饿极了的孩子忍不住偷拿了一颗枣,妇人立刻尖声指责他被邪祟附身,引来众人指指点点。生活的困苦找不到出口,只好将怨气撒在更弱小的身上。
夜幕降临时,李玥寰常能听见某些院落传来压抑的哭泣。那是将家中存粮尽数献祭后,面对空米缸发出的绝望。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会归咎于"心意不够虔诚",而非那个端坐在神庙深处的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