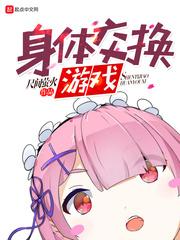奇书网>李秀成传作者李莎 > 第二节 地官丞相(第2页)
第二节 地官丞相(第2页)
双方持续战斗了十几天。
清军以守为攻,相持日久,对太平军极为不利。
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丞相商议破敌对策,决定采取与镇江吴如孝军东西合击的战术。可是清军水陆封锁通往镇江之路,无法与之联络。二十岁的陈玉成自告奋勇,乘一叶小舟,由长江顺流东下,直至镇江,与吴如孝约定时间,从城里冲出,里外配合联手发起进攻。
1856年攻破江南大营示意图
当时,李秀成等五丞相随秦日纲屯扎在汤水河西岸,与河东张国棵、吉尔杭阿军相持。清军凭险自固,李秀成乘陈仕章等尚与敌对仗时,自引本部人马三千,乘夜渡过汤水河,与来自镇江的吴如孝、陈玉成会合。次日开仗,太平军各路人马前后夹攻,清军方知后路被袭,大溃,失去营垒十六座。
张国棵和吉尔杭阿军分路溃退。
这一仗,李秀成奇兵突出,打得很好,乃是他前期的一次得意之作。对于这仗的过程,后来在供词里他还如数家珍似娓娓道来:
此是初困之救军,进镇江汤头,与张国棵连战十余日,胜负未分。后九华山清朝吉帅发兵来与张国棵会战。我亦选集锐军,两军迎敌,大战于汤头,两无法处,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按寨对扎,两不交战说话。想通救镇郡未下,当与各丞相等计议,派丞相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然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当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我带军由外打入。后查汤头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内,清军由此河边扎营。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后我天朝之军移靠汤水山边下汤头,靠河边,两家难进处所。清军营寨概移入汤水山边,堵我进兵之路。那时镇江不应绝命,吴如孝、陈玉成已由内打出。我在外高山吊望,见镇郡人马出来,旗幡明现,知是我军。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我亲带由两不能进处所,清军移堵我汤水进兵之路矣,此处无兵把守,此地叫做汤头岔河,是由此经过,将清军旧营修扎。天明原扎汤水山边之丞相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等出军与吉、张两帅制战。吉、张不知我出奇兵袭由汤头岔河而过。午未时,吉、张方知我袭其后路之信。汤头岔河隔汤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之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
李秀成记忆极好,时隔十年,还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有条不紊。若非亲身参与,苦乐相与,那是难以做到刻骨铭心的。
他确实发挥了自己固有的才智、勇敢。
此次汤水之战,前敌总指挥应该是秦日纲,但李秀成未提到他,此后也都未提到他。后来有学者认为李秀成供词未提及秦日纲,乃是一意在自扬;二瞧不起他,认为此人“并无才干”;三没有到场,或者中途因事因病离开前线。
“意在自扬”是太平天国史前辈郭廷以教授所说。笔者认同是“意在自扬”。
李秀成的供词是写给曾国藩看的。这一仗,打得很好,他要显示自己的才干,让曾国藩知道。因此时在字里行间竭力贬低清军八旗、绿营,甚至有时也贬低非湘军系统的淮军。当然,字里行间未提秦日纲,确实也有蔑视这个不识字的草包的因素。
李秀成在供词里,作如下叙述:
在获胜后,即以周胜坤部留守汤头清军旧营,其余人等乘胜东进,驻扎金山、金鸡岭和九华山脚,与吉尔杭阿大营相峙。当天夜晚,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三丞相连同吴如孝镇江军部分由金山渡江从瓜洲上陆,攻打土桥江北大营,大破清军马营,全部歼灭红桥、朴树湾、三叉河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江北大桥各支清军“那时闻风而逃,当即顺破扬州;后将扬州一带粮草运入镇江”。
太平军在江北势如砍竹。可是,后路空虚。吉尔杭阿、张国棵乘虚重陷汤头,周胜坤战死。吉尔杭阿、张国棵将旧营修理、重整,断江北李秀成等归路。李秀成等拟从扬州、仪征西走六合,上浦口渡江返天京,又因张国棵抢先一步,赶在六合阻拦,于是采取自金山渡江,回攻高资,大破清营七座。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大营来援,被打得大败,逃入高资山中。太平军四面围攻,吉尔杭阿走投无路,据李秀成获得情报,“用短洋炮当心门自行打死”。
“短洋炮”即长筒手枪,吉尔杭阿来自上海,可见军中已有部分装备外来的热兵器了。
吉尔杭阿自杀,军心大乱。李秀成等侦知敌营没有主帅,当即向九华山进发,翌日清晨,打破清营七八十座。张国棵闻讯由六合赶回,救之不及,只得在丹徒镇驻屯,李秀成等乘胜攻打,在清晨合战了几个时辰。镇江吴如孝带领千余人马前来助战,将张国棵骑兵打败,步军并进,张国棵军大败。
镇江之围全部解除。
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丞相,连续奋战一百余天,东奔西波,不辞辛劳,终于凯歌高奏。
围攻天京直接的隐患,还是驻扎周边的江南大营。
自1853年4月以来,自广西、湖南尾追的向荣兵团在天京城郊,自长江南岸北起石埠桥、中经栖霞岭、尧化门、仙鹤门、黄马群、孝陵卫、高桥门、七桥瓮、秣陵关和溧水、东坝等处,森严壁垒,盘根错节,建起一条围困线。北京王朝不断为他调兵遣将,历经三年,已拥有三万精兵。
江南大营貌若强大,实则暮气沉沉。
统帅钦差大臣湖南提督向荣,年已六十,居扎紫金山畔孝陵卫,因为脚力不便,长期卧床,不出营门一步;偶尔一次出巡,兴师动众,就向朝廷虚报功,说是打了一场胜仗。将士很难见到面,有一天张集馨前来孝陵卫大帐,向荣闻知,特地赶下山拜谒,竟引起多人惊诧不已。
统帅老朽、无能,将士军纪松懈。张集馨耳闻目睹:
孝陵卫街市,为兵勇聚集之所,又为买卖街,几于无畅不备,各兵勇与本地居民结为婚姻,生有子女,各怀家室之念;其无家者,雇土娼入帐**,后以妒争斗,闻于向帅,立斩数人,又将被雇土娼,枭于营外;似恬不畏法,昼则在田作为工作,夜则入街进帐,奸宿如常。(《道咸宦海见闻录》)
但江南大营毕竟束缚着天京,威胁安全。
杨秀清早有心把它铲除。
6月20日,镇江围解,李秀成等四丞相随秦日纲回到天京覆命。杨秀清接见,即布置立即打破江南大营,方才可以让得胜之师进京,随即令将人马暂驻在燕子矶,准备迎战江南大营。将士们满想得到休整,当时天京已允许家庭团聚,也有将士盼望能进城过多年未有的家庭生活,于此吵闹不休。秦日纲和李秀成等无奈,只得再进京向东王请示,暂不攻打江南大营。杨秀清不答应。秦日纲等在东王勒令之下,群策群力,群威群胆,一鼓作气,自6月21日全线出击。正在此时,由杨秀清自西征战场上调来的石达开军二万人赶到,东王又从天京调拨几千人马分路出南门、通济门和朝阳门,直扑七桥瓮等处,江南大营在几路人马合击下,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场大破江南大营,即是李秀成所说的“一解京围”。李秀成亲身经历,日后他有条不紊叙述这段亲历:
东王令下,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将我在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矶一带,明天屯扎,逼得无计,将兵怒骂。然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向营。我等回报,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义怒,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而行战。次日开攻,移营由燕子矶尧化门扎寨四营。尧化门清将是向帅发来镇守。我自此屯扎。次日张国棵已由丹徒返回孝陵卫,是早引军与我迎战,自辰至巳,两军并交,张军败阵,天朝之军,顺力追赶。是日张军仍回孝陵卫。我等移营,重困尧化门清营。次日张国棵复领马步前来,两家立阵相迎,各出门旗答话。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谦、张遂谋等引军到步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是日向、张所救尧化门未能,自军败阵,后被我四面追临,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独剩向帅左右数营,张国棵自扎七瓮桥,此亦剩左右剩己营也。是夜向、张自退,我天朝之兵并未追赶。
6月22日,向荣、张国棵等率残部逃往丹阳。
六七天后,李秀成等奉命追赶,在顺势取得句容后,四面包围了丹阳。向荣等以逸待劳,坚守危城以待。但失陷大营,向荣自知难逃罪责,自缢身死。
张国棵困兽犹斗,奋力打仗,太平军竟被攻破南门外营盘七个,杀死六七百人,并击死勇将、殿左十三检点周得贤。此次败局,出于骄奢,李秀成很有体会。他说:“此员战将勇敢有余,众军见此员战将战死,攻打丹阳,又不得下,各有畏意,从那时已有退缩之心矣。”
强弩之末,秦日纲因丹阳久困无效,放弃城围,撤军西南,转攻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