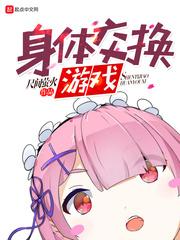奇书网>多尔衮的故事告诉我们男人 > 八 下江南(第1页)
八 下江南(第1页)
八下江南
李自成退守西安时,多尔衮为了全力歼灭李自成,还肯与南明政权假意勾搭,以免两面树敌。待李自成逃出西安,难成气候,不足以成为大清的主力敌人后,多尔衮立马对南明开战,派遣多铎马不停蹄,越过长江去。
雄心大志的多尔衮,以小搏大,虽然汉人多、满洲军民少,但他胸中自有百万兵马,他一人就可抵精锐百万。他张开双臂,要怀抱华夏。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也是这样。
多尔衮是犁平乱世的枭雄,是大英雄,也是刽子手,还是军事家、政治家。
在派遣阿济格大军追歼李自成残余军队的同时,多尔衮还要分出精力安排力量剿抚中原各地多股抗清武装。他虽注重南京弘光政权,因为南明毕竟控制着数十万水陆兵马,但多尔衮心里有数,李自成的部队最有战斗力,南明的官军貌似人多势众,其实就是个挥舞不动刀枪的大胖子,还是虚胖,外强中干,早被大清八旗军威吓酥骨了,他们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放马江南,指日可待。而且南明势力虽然暂据半壁河山,但弘光帝朱由崧只是个摆设,掌军实权不在他手里,各地军阀,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是一群群跑散的羊,头羊弘光帝有名无实,当不起大事。
果然,弘光政权被多尔衮看穿了:弘光帝朱由崧本是纨绔子弟,一路逃难到南京后,捡了个危如累卵的政权的皇帝当,因此一心想要享皇帝之乐,垂死挣扎地来玩乐,活一天,乐一天,根本不懂如何治理朝政。其实,就连殚精竭虑一心要中兴祖宗家业的崇祯皇帝也不能成功,明朝腐朽糟烂透底了,大势所趋,谁也匡扶不起来了。朱由崧无才无德,整日不理朝政,他想管也管不了,没有人听他的,是这些文武百官需要他表演皇帝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个配角。他深居禁宫,唯以演杂剧,饮火酒、**幼女为乐事,民间将他戏称为“老神仙”。当皇帝,应该掌管军事,排兵布阵,治理朝政,抚慰民生,这些他不会;他从小就在王府里混大的,吃喝玩乐全会,皇帝应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他知道,我是皇上了,我得有好多好多嫔妃宫女呀,在这项工作上,他很认真:几番选淑女,扩造宫殿,行大婚礼,他的权力和能力都在皇宫里施展,荒**无度。
总之,朱由崧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没个皇帝样。其实,他当皇帝,也是有竞争对手的:他叔叔辈的潞王朱常淓有贤德之名,以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为首的一伙人,主张立贤,史可法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东林党是明朝末年,江南士大夫们组成的官僚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历经近四十年,到明朝灭亡,东林党也瓦解。东林党以文人为主,钱谦益就是诗人,是东南诗坛盟主。历朝历代从宋朝开始,崇文抑武,武官开国,文官治世,但是到了乱世,武力决定政权时,文官主宰武将,有时误事,更会误国。此时的江南,比起笔墨战刀说了算,手握重兵的将军们,自然不会真正希望有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来控制他们,那样的话,万一皇帝不顺心,就把自己的官职剥夺了。于是,无德无才的朱由崧被武将们以血统更近朱氏皇位为由,推上了皇位,成为了众矢之的。细想想,弘光帝也委屈:我明明不行,你们硬要我上,让我承担造成南明失败的罪名。据资料记载:朱由崧南逃到长江边,四月三十日,以南京户部主事马士英为首的百官迎见朱由崧于龙舟中,请其为监国;朱由崧身穿角巾葛衣,坐于卧榻之上,推诿说自己未携宫眷一人,准备避难浙东;众臣力劝,朱由崧才同意当头儿。离龙椅血统稍远一些的潞王朱常淓,没有当上南明皇帝,却幸运地躲过了骂名。
现在,代表南明成为多尔衮的重要配角的人出现了,他不是南明皇帝,而是一个被“放逐”出南京皇城的重要大臣史可法。
南明势力范围,从长江两岸,一直到岭南和云贵川蜀,但与清军直接对阵的是江北四镇和武昌。
防御江南必须先巩固江北,主战派、兵部尚书史可法将江北防区划分为四镇:总兵刘泽清辖淮(淮安府)、海(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驻淮北,防御山东东部方向;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水(今山东南阳镇至徐州一段泗水故道沿岸),防御徐州、开封方向;总兵刘良佐辖凤(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寿(今安徽寿县),驻临准,防御陈(今河南淮阳)、杞(今河南杞县)方向;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州)、和(州治在今安徽和县),驻庐州(今合肥),防御光(今河南潢川)、固(今河南固始)方向。每镇统军约三万人。朱由崧又封左良玉为宁南侯,驻武昌,率兵防守长江中游;另有福建总兵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的部将郑鸿逵率水军守镇江;总兵吴志葵守吴淞,防长江口。此番部署,把分散在长江沿岸的军队初步统一整顿起来。但是,各镇将官只有割据自保之心,毫无进取之意,表面上人多、势众、地广,实际上形同虚设,这个防御部署从建立之日起,就暴露出覆灭的迹象。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控制着长江南北大片富庶地区,有军队五十多万。但是,政治上的草率集合体,不等于军事上的强劲实力。弘光政权内部,大多纠结于权力之争,互相排挤和打击异己,并无认真抗清的打算,而且斗争矛头仍然指向李自成的大顺军,没有认识到抗清将是关乎生死的大计。南明大权落到了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而有功的马士英手中。他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明弘光政权首辅,人称“马阁老”。马士英被讥讽为人长智短、耳软眼瞎,他勾结阉党阮大铖,联手把史可法“请”出南京,赴江北督师去了,又罢免了吕大器、张慎言等正直有经验的大臣,然后以招揽人才之名,把南京新朝组合成了自己人的圈子。
江北四镇兵马众多,朝廷无力供给,索性令四镇“兵马钱粮,皆听自行征取”。这无异是纵兵掠民,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败坏了军纪。从此各自拥兵的四镇,不听调遣,只想着争夺地盘,掠夺民脂民膏。吴三桂降清,引兵入关,绝大多数汉族官僚还天真地希望两家合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天下太平。南明政权对大顺军刻骨仇恨,对清军抱有幻想,史可法就是其中的代表。
多尔衮向明朝的降官们咨询了解南明政权要员们的情形,得知史可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先礼后兵,于七月二十八日致书史可法,大意为:“我大清国抚定燕都,是得之于李自成,并非取之于明朝。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而今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我将简西行之师,转而东征。诸君子如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先生乃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我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我实有厚望矣!”
有人称赞此信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信中一针见血,剖析当前面临的军事形势,说明了弘光政权虽偏安一方,对清廷统一全国是极为不利的。多尔衮以正统自居,公开申明大清是华夏的新任朝代,自家是最高统治者,毫不掩饰地承认清廷要君临天下。他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寄希望于和平解决江南问题,要求南明君臣无条件投降,也做好了武力征服的准备,甚至扬言“联闯平南”,要联合大顺军一起来攻打南明,这是多尔衮以谎言相威胁了。当时尖锐的政局矛盾为多尔衮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也巧妙地钻了空子,利用了汉族各集团间的矛盾冲突,为清朝统治集团制定了最高超的战略方针。
多尔衮最初也是冒进狂热的,可能是被山海关大战和入主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想双管齐下,同时进攻大顺军和南明小朝廷,速战速决,以最快的速度占有中原及长江南北广大地区。因为大顺军发动了怀庆战役,清军吃了亏,多尔衮才顾虑到兵员不足,战线过长,及时调整进攻方略,把兵锋矛头集中,先重点打垮李自成,因而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怀柔、招抚、谈判的手段,尽量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能奏效就好,不能,就拖延南明,免得南明醒悟过来,趁清军与大顺军对决时,从侧背后突袭清军。那样的话,清军会腹背受敌,是很不利的。
况且,归降大清的明朝遗臣们,都在官场厮混成老油条了,对上级的想法揣摩得深刻精准,看透了大清的野心,知道摄政王的难处,于是,有些人为了讨好多尔衮,上疏建言各种军政时务。
前明降官唐虞时自告奋勇地向多尔衮建议:“南京是形胜之地,闽、浙、江、广各地,都看南京是否降顺来决定他们的态度,如今应乘他们害怕不安的时候,颁布令旨和赏格,让人带到南京去,宣谕官民,江南之地可传檄而下。”唐虞时又说,“原来的总兵陈洪范可以招抚,我的儿子唐起龙是陈的女婿,又曾做过史可法的参将,江南的将领他大多相识,希望派他前去招降,这样统一大业就能成功”。多尔衮一看:“好啊!如此甚好。”多尔衮亲自致书陈洪范,希望他归顺。多尔衮还对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发布诏谕,表示对他们的归顺不仅欢迎,还将赐官封爵,以勠力同心,共保江山。多尔衮同时又表示:“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假心假意,行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等到我军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多尔衮对南明的所有官员祭出了同一法宝:一面行笼络利诱之策,一面施威胁诡诈之计,旨在争取时间,避免在消灭李自成之前出现南明与大顺军联兵抗清的不利局面。多尔衮的担心是正确的,后来,大顺军余部和南明抗清势力果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清军了。
在山东替清廷进行招抚的王鳌永,于七月二十日向多尔衮报告:“南方各镇总兵都在江北驻扎,江北为必争之地,徐淮属城皆跨河南北,尤宜早图,以控扼徐淮。”多尔衮明白:“只是简单地派人到南方去招抚,决不能达到传檄而下的结果,必须对南明政权加以试探,同时窥测南方的军备、政治等状况,等待大清八旗满、蒙、汉军兵腾出手,横扫江南,才是彻底解决之时。”
史可法接到多尔衮的信,阅罢,忧心忡忡,作为大明忠臣,他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大明朝,即便这个国家已被大顺军推翻,他和同僚们也只肯认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失利,不愿意承认是总体上垮掉了、没有未来了。明知清军是虎狼,比大顺军更凶猛,史可法他们仍然幻想着如同史上一些特殊时期那样,南北共治,各安其国。九月十五日,史可法无奈地复信多尔衮,信中明确表示:“弘光政权是名正言顺的明朝政权,绝对不会投降,而是要继续保持明朝的统治,希望清军全力镇压大顺军,但事毕后须撤退返师,仍为两国。”他还大义凛然警告多尔衮,“不可乘机占据明朝疆土。弘光政权即使感谢,也不会拿土地送礼”。史可法的严正立场代表了南明抗清派的要求,但南明内部并不协调,抵抗派、投降派、调和派等各种意见众议成林。
在多尔衮看来,史可法这种希求简直是无稽之谈。
史可法虽然为弘光朝廷继承正统的合法性进行了申辩,却拿不出对付清军的办法。
多尔衮这边,从来就没把仓促草率创建的南明政权太放在眼里,认为不过是乌合之众。对南明派来的修好使团,多尔衮冷眼相看,虽然喜欢南明赠送的大宗慰问礼品,不过也是因为眼下清廷正缺少财物,其实也没当回事儿。在多尔衮的影响下,清廷朝臣们把作为国书交流的弘光帝御书呼为“进贡文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多尔衮想要的是清廷一统天下,当招抚不能解决问题时,那就只能以兵戎相见了。
顺治元年(1644)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劝说多尔衮:“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江南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历来都是南粮漕运养北京。只有这样,大清的财政税银方一劳永逸。”这更促使多尔衮立马着手取江南。
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七,多铎分兵三路:一路出虎牢关,一路由固山额真拜尹图指挥出龙门关,另一路蒙古兵由兵部尚书韩岱等统领走南阳,驰骋在中原大地,势不可当。
三月初一,有自称崇祯太子朱慈烺者至南京。弘光帝朱由崧命令将其关入兵马司监狱,后命百官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终裁断为伪太子,名叫王之明。
四月,马士英和阮大铖在朝中弄权日盛,乌烟瘴气。
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率领主力军二十余万,粮饷无着,士卒竟有饿死者。加上长期受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打击,以及东林党人的鼓动,他自称奉太子密诏,打出“救太子、清君侧、除马阮”的旗号,焚武昌城,顺流东下,进攻南京。
南明发生了内讧。内忧外患,使弘光政权恐慌不安、手足无措。马士英竟然命令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马士英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主张防御淮扬一线的文武臣僚破口大骂:“你们这伙东林党,想借防江纵左军进犯!清兵到了还可以议和,左逆到了,你们是高官,我君臣却得死!我们宁可死在清兵手里,也不死在左兵手中。”史可法只得抽调黄得功、刘良佐部抵御左军,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镇守江北的史可法,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孤掌难鸣,气愤地说:“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奸臣当道,忠诚难酬。左良玉兵至九江,为黄得功所败,吐血而死。其子左梦庚愤怒至极:“大军留守武昌,若不掠夺民生,全体将士就会饿死,今‘清君侧’不成,那么也就不要再为南明卖命了。”一赌气,他率全军转投清朝。
多铎率清军前锋进入安徽,相继攻克颖州、太和等城镇。多铎命令将士们休整十天,再度南进,经亳州、泗州,如入无人之境,直抵淮河。南明守兵不战而退,焚毁淮河桥,望风而逃。清军越战越勇,不辞劳苦,夜渡淮河,追击南军,不给溃兵以喘息之机。在强大的清军进攻面前,南明守江北的军队败的败、降的降、逃的逃,所有的防御部署全部被破坏。军情紧急,史可法惊慌失措,毫无主见,一日三发令箭,前后矛盾。将士们纷纷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增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刘良佐和高杰部的将领,相继不战而降。史可法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节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十八日,兵临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