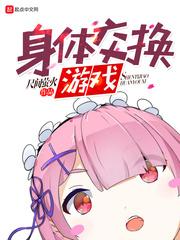奇书网>星渡银河 > 扬名惊四座(第2页)
扬名惊四座(第2页)
“第二步,将七升壶中之酒,倒满三升壶。此时,十升壶剩三升,七升壶剩四升,三升壶满。”
“第三步,将三升壶中之酒,全部倒回十升壶。此时,十升壶有六升,七升壶剩四升,三升壶空。”
“最后,将七升壶中之酒,再次倒满三升壶。七升壶中恰好剩余……一升?”
她话音一顿,微微蹙眉,随即立刻修正,“不对,七升壶原剩四升,倒满三升壶后,应剩余一升。但我们需要五升……”
她瞬间意识到计算有误,但思路并未打断,立刻重新推演:“更正。第二步后,状态为十升壶三升,七升壶四升,三升壶满。第三步,将三升壶酒倒回十升壶,十升壶为六升。第四步,将七升壶的四升酒倒入三升壶至满,七升壶则剩一升。第五步,将三升壶酒再次倒回十升壶,十升壶则为六加三,共九升。第六步,将七升壶剩余的一升酒倒入三升壶。第七步,从十升壶倒酒填满七升壶(十升壶原九升,倒出七升,剩二升)。第八步,用七升壶的酒倒满三升壶(七升壶原七升,倒出二升给三升壶,三升壶原有一升,加二升满,七升壶则剩五升)。”
她语速平稳,逻辑缜密,一步步将复杂的倒酒过程清晰道出,最终指向目标:“如此,七升壶中,便是所需的五升酒。”
整个流觞亭鸦雀无声。众人已被这一连串的“倒来倒去”绕晕,但看她笃定的神色和无可挑剔的逻辑,心知答案必然正确。
琉球正使深深地看着苏浅陌,眼中的轻视已完全被震惊取代。他沉默片刻,躬身道:“……分毫不差。凰月果然人才济济,外臣拜服。”
(第三题:暗讽与机锋)
连续两题被破,琉球使团气势受挫。那副使心有不甘,再次起身,这次却不再出具体难题,而是带着一丝挑衅开口道:
“最后一题,外臣想请教这位女史。我琉球虽小,亦有古训:‘水能载舟,亦能煮鱼’。不知贵国以女子之身驾驭如此庞大的帝国,如舟行巨浪,可知‘水’之性情?又如何确保这‘舟’永不倾覆?”
此言一出,满场皆惊!这已近乎赤裸裸的质疑女皇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翰林院官员面露怒色,却一时不知如何驳斥这刁钻的隐喻。
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看向苏浅陌。
苏浅陌感受到来自御座方向那道平静却极具分量的目光。她知道,这个问题,已远超智巧,关乎国体。
她深吸一口气,迎向琉球副使,目光清正,不闪不避:
“使臣大人所言‘水能载舟,亦能煮鱼’,颇具哲理。然,我凰月对此另有理解。”
“在我朝,万民非‘水’,陛下亦非‘舟’。”她声音抬高,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陛下乃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星辰环绕北辰,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共耀天穹,何来倾覆之忧?”她顿了顿,语气转而凌厉,“至于‘煮鱼’之喻,更是荒谬!我凰月君臣一心,万民同德,如同星辰辉映,光明坦荡。唯有心怀叵测、暗藏沟壑者,才会以‘水火’之险来揣度煌煌天朝!”
她不仅巧妙化解了“舟水”的被动比喻,将女皇置于至高无上的“北辰”之位,更反将一军,暗指琉球使臣心存叵测!
“你!”琉球副使脸色涨红,一时语塞。
“好!”席间不知哪位大臣忍不住低喝一声彩。
洛长羲端坐其上,看着场中那个身姿挺拔、言语掷地有声的女子,看着她为自己、为王朝辩护时眼中那不容置疑的光彩。一直平静无波的眸底,终于漾开了一丝清晰的、名为欣赏的涟漪。
她缓缓开口,为这场交锋定下基调:“苏女史所言,正是朕心之所想。使臣,可还有疑问?”
琉球正使连忙起身,扯了扯副使的衣袖,躬身道:“陛下息怒,副使失言,外臣代其赔罪。凰月人杰地灵,外臣等今日大开眼界,心服口服!”
宴席继续,但气氛已然不同。琉球使团变得格外恭顺,而凰月众臣再看向那位角落里的苏浅陌时,目光已充满了惊叹与复杂。
苏浅陌坐回案后,重新拿起笔,仿佛刚才那个锋芒毕露的人不是自己。只有微微颤抖的指尖,泄露了她内心的激荡。
她知道,也许以后,她将不再仅仅是尚宫局一个特殊的女史。
“苏浅陌……”洛长羲在心中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目光掠过她低垂的、露出纤细后颈的侧影,随即若无其事地移开,与身旁的我低语了几句。
我看着好友,心中既自豪又隐忧。晓月如同蒙尘的明珠,正在被迅速拭去尘埃,光华灼灼,却也意味着,她将吸引更多目光,承受更多明枪暗箭。
凤鸣于庭,声动四方。是福是祸,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