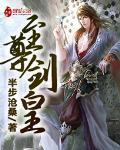奇书网>汴京怎么被攻陷的 > 第十三章 春耕谋定后动(第1页)
第十三章 春耕谋定后动(第1页)
正月过后,汴京的寒意渐消,金水河畔的柳枝抽出了鹅黄的嫩芽。陈启明与林静换下节日的盛装,重新穿上便于行动的棉布衣衫,将目光投向了西郊的白杨村。元宵的灯火犹在眼前闪烁,但两人深知,那璀璨只是一瞬,脚下的土地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二月初,春寒料峭,度支司内还弥漫着年节的闲适气息,同僚们正在交换着年节见闻。陈启明却已伏在案前,对着他精心绘制的《白杨村试验田轮作时序图》进行最后的斟酌。图上清晰地划分着两个区域,旁书八字纲领:“双轨并行,时序交错”。
放衙的梆子一响,他便快马出城,直奔白杨村。田边小院里,林静正与周老丈及几位雇工围着一台崭新的耧车。
“程官人来得正好!”周老丈指着耧车,满脸兴奋,“小娘子改良的这宝贝,老汉试过了,播下的种子又直又匀,深浅得当,比旧式强出何止一倍!”
林静挽着袖子,正在调整播种箱的插板:“王师傅的手艺确实精到。不过还要试试播豆子的效果。”她抬头看见陈启明,眼中闪着专业的光芒,“豆粒比粟米大得多,需得换个漏孔。”
陈启明笑着将手中的图卷在院中的木桌上摊开:“器具要改良,田亩也要规划。我有个想法,说与老丈参详。”
他指着图纸:“这十亩地,咱们分作两区。五亩为粟区,今春播粟,秋后种麦,来年夏收后种豆;另五亩为麦区,今春就种豆,秋后同样种麦,来年却种粟。”
周老丈闻言,花白的眉毛顿时拧成了结:“这……麦区春播豆子?程官人,不是老汉多嘴,这豆子向来是麦收后抢种的,哪有开春就下地的?这不合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啊!”
“老丈说得是。”陈启明不慌不忙,“正因如此,咱们才要试试。”他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您想,若是春豆能成,秋后种麦时,地力已被豆子养得足足的。来年这麦子的长势,定比寻常田地更旺。”
林静放下手中的工具,走过来补充道:“豆科作物根系特殊,能固氮……嗯,按古书记载,是能吸纳天地精气反哺土壤。《齐民要术》有云:‘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
“《齐民要术》?”周老丈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书里真这么写?”
“后魏贾思勰所著,千真万确。”陈启明肯定道,“咱们麦区试种春豆,正是循古法而创新。若成,则白杨村又多一条增产的路子;若不成,损失也有限。”
周老丈沉吟良久,猛地一拍大腿:“成!就依二位官人、娘子的法子!老汉我也开开眼,看看这春豆到底能长成啥样!”
二月中的白杨村,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忙碌景象。
林静整日泡在工匠处,与老木匠反复调试着耧车的排种器。她设计了两种可替换的漏盘,一种专播细小的粟米,一种专播滚圆的豆粒。又指导铁匠将犁铧重新锻打,角度更趋合理。
“妙啊!”试用新犁的雇工忍不住赞叹,“这犁轻巧,翻地却深,比旧犁省力多了!”
陈启明则发挥其经济专长,制定了一份详尽的《雇工章程》。他创新地引入了“工分制”,将翻地、修渠、施肥等不同工种的劳动强度量化,每日登记。
起初,村民们对这个新制度将信将疑。
“什么工分不分分的,能给现钱才是正经!”
“就是,别到时候白忙活一场。。。。。。”
陈启明不急不躁,将章程一条条解释清楚:“每日工钱照发,工分另外计算,秋收后按工分红。干得多、干得好的,分的就多。”
为了取信于人,他当场预支了第一旬的工钱。见到真金白银,村民们的疑虑渐渐打消,干活也格外卖力起来。
二月末,一切准备就绪。新修的沟渠纵横交错,在春日下泛着粼粼波光;改良的农具整齐排列,随时待命;雇工们经过培训,个个摩拳擦掌。
执法记录仪在这期间发挥了特殊作用。每隔一段时间,陈启明总会借口“勘察地形”,在田间行走,用记录仪秘密拍下土壤状况、沟渠布局。在夜深人静时,他与林静反复观看这些影像,分析着每一块田地的细微差别。
三月伊始,春暖花开,终于到了播种的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