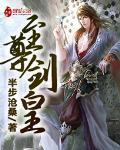奇书网>汴京指的哪 > 第十四章 夏耘暗涌(第1页)
第十四章 夏耘暗涌(第1页)
太平兴国九年,夏初,阳光正好,万物疯长。白杨村的试验田与周边田地,已是泾渭分明。
陈启明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这幅生动的画卷。属于他的十亩试验田里,粟区的粟苗,经历了间苗、除草和一次追肥(用的是林静指导沤制的稀薄液肥),苗秆挺拔茁壮,叶片肥厚宽大,颜色深绿欲滴,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特别是经过林静指导施肥的田块,长势更是喜人,整齐的田垄宛如铺开的绿色锦缎。
麦区的春大豆更是成了村里的一景。当初的质疑者,如今都围在田边啧啧称奇。豆苗植株健壮,已然开花,淡紫色的蝶形小花点缀在绿叶间,预示着不久后的丰收。这成功印证了“春播豆类”的可行性,也让林静在村民心中“格物大家”的形象更加稳固。
而真正核心的变化,藏在由周成精心照料的“药材圃”(即战略研发区)里。对外,这里种的是些“海外引种的奇特药草”。实际上,那些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块茎——土豆和红薯,藤蔓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疯狂蔓延,绿意盎然,长势之旺盛,连周成这个半大小子都时常看得目瞪口呆,只按照林静的吩咐,小心翼翼地培土、除草,不敢多问,心头却充满了对未知收获的期待。
而紧邻的农户田地,粟苗却稀疏发黄,高低参差,像是被随意撒在土里的野草。
“程官人,您瞧见没有?”周老丈兴奋地指着田埂,“咱们的苗,比旁边的足足高出一指!这才一个月的光景,差距就这般明显了。”
几个正在邻田除草的农户也直起腰来,羡慕地望着这边。有人忍不住问道:“周老叔,您这田里是施了什么仙法?怎地长得这般好?”
周老丈捋着胡须,脸上带着藏不住的笑意:“哪有什么仙法!就是程官人、程娘子教的法子——深耕细作,科学施肥。你们若是想学,秋收后老夫可以帮你们说道说道。”
这生机勃勃的画面,却让陈启明脑中浮现出前几日度支司内截然不同的场景。
度支司内,算盘声噼啪作响,气氛却比往年此时更加凝重。新一年的预算核算如期而至,这不仅是案牍劳形,更是各方势力角力的开端。陈启明埋首于浩如烟海的账册之中,眉头紧锁。他负责核验的部分,恰与河北路边军粮草调度密切相关,数额巨大,条目纷繁。
副使钱有财端着茶盏,慢悠悠地踱到陈启明案前,随手拿起一本他刚核验完的账册,翻了两页,皮笑肉不笑地说:“程司吏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这军国大事的账目,核验起来竟如此迅捷?听说你在西郊置办了田产,想必是城外山水养人啊。”周围的几个书吏都竖起了耳朵:“难怪总是告假。也是,这田庄之事,确实比度支司的公务要紧得多。”
这话夹枪带棒,既点出他“不务正业”,又暗含威胁。陈启明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恭敬答道:“钱副使说笑了。下官休沐日去田间,是为验证《齐民要术》中所载轮作之法。若此法能成,或可裨益国用,不敢因私废公。。”
“哦?轮作?”钱有财嗤笑一声,“老祖宗传了千年的法子,还需你一个后生去‘验证’?还是多把心思放在这河北路的军粮预算上是正经!如今北边风声紧,若是出了纰漏,你我项上人头,怕都担待不起。”他刻意加重了“河北路军粮”几字,语带威胁,方才甩袖离去。
话说到这个份上,陈启明只能躬身称是。待钱有财走后,他才缓缓坐回位子,指尖在算盘上轻轻划过。
确实,最近河北路的军粮预算有些异样。几笔采买的价格微妙地高于市价,而出粜陈粮的价格又偏低。更让他注意的是,雄州、霸州等边州的仓廪修缮预算突然增加,理由都是“防秋汛”“固根本”。
种种迹象,都透着不寻常。
这时,孔目官张茂拿着一份文书过来,声音平和却足以让周围几人听见:“启明,正要寻你。漕司移来文书,需人前往郑州左近,核对几处常平仓的储粮数目与周转情况,来回约需三四日。此事务必仔细,我看……此事交由你办最为妥当。”他说着,将文书递过,状似随意地低声道:“路上若见什么农事新法,亦可顺便观摩,回来也好说道说道。”
陈启明心领神会,这是上司在不动声色地为他创造合理离开衙署、前往白杨村的契机,且公干之名,正大光明。“下官领命,定当仔细核查,不负所托。”
不同于陈启明的“公干”,林静在盐铁司胄案的处境则稍显宽松。她“作作”的职掌本就包含查验物料、核验工匠成果,需要不时前往库房、工坊。这一日,她正欲出门前往将作监的一处作坊,查看新一批箭簇的淬火情况。
同僚中一名与孙侍郎有些瓜葛的主事,见状便阴阳怪气地笑道:“程娘子这是又要去‘格物’了?当真勤勉。”言语间不无讥讽。
恰在此时,冯纶从廊下经过,闻言停下脚步,面色平淡却语气坚定地说道:“程娘子精于辨识,于物料火候别有心得,其所察所验,于兵器质效提升大有裨益。胄案事务,贵在务实,能者多劳,何来闲言?”他目光扫过那主事,后者立刻噤声,讷讷退下。冯纶转而向林静微微颔首:“程娘子自去忙,若有需协处,尽管来寻我。”
有了冯纶的明确支持,林静在胄案的行动少了许多掣肘。她可以更自由地往来于衙署与白杨村之间,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田间管理与她更关注的兵器改良试验上。
眼下林静正与周老丈在田头忙碌。原来,她在巡视时,敏锐地发现了粟区粟田中零星出现的粟瘟病初期症状。
“已按娘子的吩咐,将病株移除焚毁,也喷洒了药液。”周老丈汇报着,心有余悸,“若非发现得早,这一片好庄稼怕是要遭殃!”
林静蹲在地上,检查着喷药后的叶片,头也不抬地说:“治理病害,贵在早察、对症、根除。虫卵病菌,皆潜藏于细微之处,若待其坐大蔓延,便悔之晚矣。”
陈启明望着她专注的侧影,心中凛然。这话,仿佛不仅是说给周老丈听。度支司预算中的那些微妙“病症”,朝堂上针对他的那些流言“虫害”,不也正需要这般及早洞察,精准应对吗?
陈启明正出神看向远方,眼神对上了再次前来“顺路看看”的冯纶。
两人站在田埂上,望着长势迥异的庄稼,冯纶眼中不掩赞赏:“程司吏,看来你这‘双轨并进’之法,初见成效啊。赵……上面,对此很是满意。”他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不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听闻,孙侍郎那边,已有人对你在白杨村之事多有非议,言你‘不修本职,专营私田,结交乡野,其心难测’。”
陈启明心头一凛,知道真正的麻烦来了。他躬身道:“多谢冯大人提点。下官惶恐,此间诸事,皆是为验证农法,若于国于民有利,下官愿将所获尽数呈报。”
冯纶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你有此心便好。只是,有时‘利’太大,反倒成了取祸之道。你好自为之,秋收之前,务必谨慎,莫要授人以柄。”他顿了顿,补充道,“尤其是那些……过于‘奇特’之物,在能说明其来历、定性其功过之前,不宜过早现于人间。”
这话,几乎是明示了秘密试验田的存在已非绝对秘密,至少引起了赵普一系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保护性警惕。
送走冯纶,夜幕下,田边小院中,兄妹二人交换着日间际遇。
“看来我这‘病’还得装下去,”陈启明苦笑,“多亏张孔目周全。”
“冯孔目也替我挡了些闲话。”林静接口,随即话锋一转,“但依赖上司回护,终非长久之计。就像这田,药液能救一时,终究要靠自身苗壮,方能抵御病害。”
“我明白。”陈启明望向窗外无边的黑暗,以及黑暗中那片孕育着希望与危机的土地,“待到秋收,颗粒满仓之时,才是我们真正能站稳之时。”
初夏夜风带着泥土与药液的气息,官场的暗涌与田间的生机,在这片星空下无声地交织、角力。
春风拂过田野,新修的毛渠水光潋滟。在这片千年之前的土地上,知识与传统碰撞出的火花,已悄然落进泥土,静待着一场破土而出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