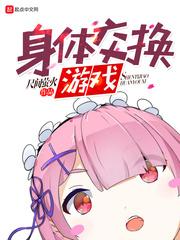奇书网>汴京城复原图 > 第三章 绝境方舟与妥协之始(第2页)
第三章 绝境方舟与妥协之始(第2页)
陈启明郑重点头:“所以,我们必须得和办案一样,慎用每一次‘进入’机会。”
规则的明确带来了稳定感,也带来了束缚。他们利用最初几次宝贵的机会,取出了少量压缩饼干、矿泉水以及一些拆去包装的常用药品,生存条件得到初步改善。随后,他们将剩余的进入机会,全部投入到近乎绝望的回归尝试中。
他们回到降临地点反复搜寻,徒劳无功。
他们冒险接近可能与仓库门对应的城墙段落,除了森严守卫,一无所获。
他们甚至尝试在月下手持书稿默念咒语,或是在精神极限时想象回归瞬间……所有努力,石沉大海。
希望,在一次次的徒劳中磨损、消耗。
屋漏偏逢连夜雨。或许是心力交瘁,加上水土不服,陈启明在一次淋雨后发起了高烧,意识模糊,浑身滚烫。古代的医疗条件让他们不敢轻易求助,而退烧的现代药物,都在空间里。
“还剩最后一次本周期的进入机会。”林静看着因高烧而胡言乱语的陈启明,又看了看那本手稿,内心陷入了巨大的挣扎。这最后一次机会,是用来继续寻找可能渺茫的回归线索,还是用来救命?
没有犹豫太久,她深吸一口气,紧握书册。
“等我回来。”
她消失在庙中。在相对静止的空间里,她争分夺秒地找到抗生素和退烧药,小心地撕掉所有外包装,用干净的布料包好。在心悸和晕眩感刚刚袭来时,她带着药品及时返回。
药片顺着清水喂下,陈启明的呼吸逐渐平稳,沉沉睡去。林静守着他,看着窗外泛白的天空,手中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药片铝箔板。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与明悟同时涌上心头:回去的路,或许真的没有了。这个粗糙、艰难、危机四伏的宋朝,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全部现实。
几天后,陈启明病愈。两人坐在庙门口,望着汴京城内升起的袅袅炊烟,进行了一场决定未来的对话。
“回不去了,老陈。”
陈启明沉默着,缓缓点头。脑海里回放着河边艰难拉纤的夫子,集市里锱铢必较的商贩,最终落回手中那本仿佛承载着他们命运的手稿上。
“既然回不去,”陈启明翻动手稿,目光变得锐利而务实,“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活着。我们要在这里,好好地活下去,甚至……活出个样子来,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手稿上写的那些事情发生。”
他翻动手稿,目光不再局限于那些狂想的计划,而是开始用经济学的眼光,审视其中关于汴京物价、行会结构、物流漕运的零星信息。他猛地抬起头,眼中之前的迷茫与恐慌已被一种沉静而坚定的光芒取代。
他看向林静:“‘方舟’是我们的底牌,手稿是我们的情报。赵铭用疯狂的方式失败了,我们要用更聪明的方式。”
他语气果断,如同在制定一份长远规划,“当前阶段,目标是:利用最低限度的空间资源,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在汴京城站稳脚跟,获取合法身份和稳定收入。”
林静点了点头,理工科的务实特质让她立刻抓住了核心:“明白。第一步,是利用现有资源解决身份和启动资金。我们需要一个经得起查验的来历,以及一份能融入这里,并能接触到更多信息的营生。”
妥协,在此刻不再是无奈的屈服,而是基于理性判断和严密规则下的战略转向。他们不再是意外坠落的迷途者,而是手握剧本、意图逆天改命的执棋者。
属于他们的《汴京案卷》,关于生存与发展的第一章,正式揭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