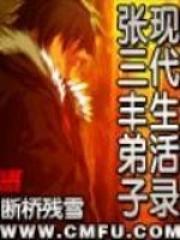奇书网>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与韦伯意识形态批判的比较(第1页)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与韦伯意识形态批判的比较(第1页)
第三节对马克思与韦伯意识形态批判的比较
马克思与韦伯都承认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但二者对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独立性却持有不同的见解。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韦伯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合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
一、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将意识形态视为现代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又是历史唯物主义构架的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1]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虽然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能否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否则,就会像机械唯物主义那样,陷入诸如“人创造环境”还是“人是环境的产物”的怪圈。只有肯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并承认其能动作用,才能理解“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62]。正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3]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领域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有意识地活动着的人,这种人的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其中无疑包括“对人的动机、目的、意识和全部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认可”[64]。只看到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地位,而无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会使历史唯物主义沦为机械的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一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经济因素绝非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这里还包括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65],其意图就是为了阐明意识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韦伯认为,现代文化与现代制度一样,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此来说明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新教伦理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入经济领域,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他在为宗教社会学撰写的“总序”中指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不仅探讨了“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具体分析了“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66]。可见,韦伯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重要作用。
二、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与独立性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的内容来源于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迁。因此,意识形态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7]只有社会存在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基础地位,而意识形态不过是“观念副本”而已,“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8]。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考察始终不离开社会存在,他从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寻找意识形态的根基。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先进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落后的或反动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延缓社会历史的进步。为此,马克思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69]。
在韦伯那里,文化论与制度论作为现代性研究同等重要的两大主题,不存在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同等重要的,不存在一方决定另一方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文化并不依赖于现代制度,意识形态也不依附于社会存在。因此,现代意识形态就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立领域。特别是韦伯通过对现代性文化的考察,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合理化原则,这样,就将意识形态作为合理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加以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依附于社会存在,那么对意识形态的考察势必要从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寻找意识形态的根基,这就把意识形态纳入某种与社会存在的关联性中加以研究。在卢卡奇那里,这表现为将现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现代商品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意识归结为商品生产的“物化现象”所造成的“物化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认定现代意识形态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这样,就在对现代商品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辩证地说明了“物化意识”的现实根源。然而,卢卡奇却把现代社会生活领域的合理化原则,直接运用于意识形态批判之中。他谈道,只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探讨一下一方面作为对象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看清楚资本主义及其灭亡的意识形态问题”[70]。卢卡奇的这种做法,是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中寻找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源,然后将社会存在中的合理化原则直接运用到社会意识领域。我们已经很难区分出卢卡奇那里的商品交换中的合理化原则和现代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化原则,现实社会中的既存事实与意识形态中的观念反映都被归纳为同样的“物化”。他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以合理化来展开意识形态批判不得不承认是更多地借鉴了韦伯的理论。这就造成在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上,卢卡奇立足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架构,却采取韦伯的合理化分析这一独特的进路。
[1]〔德〕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71页。
[2]〔英〕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1页。
[3]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页。
[4]〔德〕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65、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
[7]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61页。
[8]〔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第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15页。
[10]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64页。
[1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64—6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9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3—7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7页。
[21]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56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9页。
[2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6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5、48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7—8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5、48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11页。